
馬建: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政治環境
中國社會正處在由無產階級專政往資本主義專制的過渡期。執政者己由殺富濟貧,轉為殺貧濟富。己演變為資產者的代言人。但政治核心依然不變。等於進入了當年蔣介石式的极權統治時期。中國人在本世紀是處在很不同的社會環境里,中國當代文學特征也是社會特征的再現。作家和文學作品都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當代的漢語文學主要由三個不同的社會──中國、台灣和香港為主而形成的。同時,也包括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文學。由於高行健代表流亡文學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突顯了文學與社會政治環境的重要。假如他的兩部代表作品在中國寫完並出版。一定無法展示個人心靈的坦然。也就和今天中國的文學沒什么區別。頂多証實了极權政治也有文學這种職業而己。
中國的文學和個人的現實斷裂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當代文學特點,是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作家們試圖以文字,表達對共產党社會的贊揚或不滿。談不上走進個人的現實。中國的當代文學由八十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才開始形成。但還都脫离不了政治控制的桎梏。社會只存在共產党的現實,沒有個人現實的生存機會。台灣和香港在六十年代就己經出現翻譯加謬的《局外人》等現代作品。早形成了從模仿到個人風格形成的環境。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己找到了作家個人的社會位置。
五十年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被共產党整肅到邊疆或者下放為工人和農民。沈從文也不敢從文了,悄然沈默下來。生活在城市並可以寫作的只有幾個左派作家。他們的職業其實不算作家,只能算政党宣傳家。像賀敬之、郭沬若、艾青等人。老舍為了迎合共產党,干脆把從前的小說再改寫,以配合党的要求。他們几乎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人的事業中了。
六十年代初,特別是文革期間,中國知識份子開始以筆代刀,以最漂亮的大字報方式,展開了文人相克的斗爭。這些人物有的從左派變右派,有的從右派變左派,但都互相以誰真正愛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來互相殘殺。曹禺、巴金、老舍、丁玲等人都是那一代的犧牲品。作家處在恐懼和虛假之中,創作不了什么文學作品。所謂的社會主義文學不外乎是些《雙槍老太婆》、《金光大道》等,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龍須溝》、《青春之歌》等更虛假。
七十年代,經過了幾次死里逃生之後,活下來的作家或者叫文化人,重組了中國文學界。雖然己經快進入八十年代了,共產党才發現要抓商品經濟,也希望文學藝朮開放些。但這些文化人骨子里是多年的党的干部。青年時代都是把生命獻給共產主義的革命者,他們先天對資產階級有本能的反感。允許作家自由創作只是表現他們的心胸開闊點而已。在七十年代,“創作自由”不是行不行的問題,是和“打倒毛主席”一樣,都是反革命口號。抓到說話者就投進監獄。當代文學就是在反對這些人的控制中滋生出來的。
首先在社會環境里出現的應該是一种文化現象,繼而才算是文學現象;一些平反的右派們開始寫文章控訴自己受的苦,是可以查到的真人真事。他們叫:傷痕文學。這一批作家的特點,都是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寫作的。所以,他們面對的困境是:從失敗的教條主義中,尋找出自己被枉了的事實,而不是個人的存在價值。作品內容表達了對被迫害的不滿,也表示給他們平反的現執政者對了。他們還是認為共產党是偉大光榮,只是不正確,有些時候犯了錯誤而己。在當時,誰的傷痕又深又長,誰就是英雄。沒有傷痕就不是作家。經歷大都出色過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像白樺、劉賓雁、叢維熙、王蒙、張賢亮等都是這么成為作家的。因為從党的主席到文化部的部長,都是帶著大傷才能當大官的。受苦、訴苦、比苦,以苦為榮,以苦為業,成了這些作家的創作能源。也就是說,沒有自身受苦,也就沒有作品,沒受苦也當不了作家。受苦變成了對党忠心的一次次考驗。老舍投湖自殺還要把毛主席語錄放在身上。
社會主義文學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作家群体基本上都是共產党員。給予平反的原因是他們並沒有反党。把左派打成右派是個錯誤。至今沒有一個打成右派的作家堅持自己的立場,要求不平反,以証實自己确實是右派,既反對党的領導也反對社會主義專制。沒有。這些摘了右派帽子重新恢復了党籍的左派們,同時也都是掌握文化權力的人物。雖然他們並不完全相信共產主義了,但政府給了他們社會地位和權力。比如中國的《收獲》文學雜誌社,按党的規定,党員的比例不少于四人。當一位老党員編輯退休了,再進入編輯部工作的人,只能是党員。這些制度的設定者是為了党的利益,而不是文學的發展而工作。他們主要是配合党的政策,又發表些不触及現實根本問題的作品,形成社會主義文藝陣營,與軍事陣營合壁,一文一武,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消除資產階級思想和持個人創作自由意識的人,也是左派作家的專職工作。
這一批作家其實還和當代文學扯不上關系。他們的作品大都是右派平了反,寫受苦經歷。符合党對那些年代的不滿。反思過去,放下包袱,都是在証實今天執政者的正确。這就出現了反思文學。憶苦思甜,吃水不忘打井人,把過去描寫的越苦,今天的政府就越好。有個別的作家趁机在字里行間,表達點對党的反感,有的甚至指桑罵槐批評政府。這些文人的小造反、小聰明,加上欲言又止、含沙射影、模稜兩可和語意模糊的漢語的特點,出現了大批似是而非的一代作家。像馮驥才、張潔、蔣子龍等,都是傷痕加反思的混合。這些人深思又熟慮,狡兔三窟,走中庸之道,模稜兩可,既似乎關心社會變革,又實則保護自身的地位。同時是文化戰線的共產党員,又是給党提意見的作家,体現了政党和作家可以同体生存的後极權主義的環境。難听點說,這些人本身對自己沒自信,也膽小。沒有一套個人的思想往深了走。便只能靠依附在政府給的社會地位里生活著。對社會和政治的看法只能投機取巧。也叫隨遇而安。几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有一些職稱:如作協主席、文聯秘書長、文化局長等。沒有一個純粹的作家。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產生的作家,是繼右派平反文學之後,發展的新一代。他們沒有右派監獄勞改式的傷痕,但都被送到農村生活,有城市人到農村的生活反差,有被社會拋棄的痛苦,也有野蠻和原始愚昧與現代人的沖撞。錯位和失落又養出了新一代作家。于是,在八十年代,為了表達他們的受苦經歷,出現了描寫知青生活為主的尋根文學,因為只有以農村和大自然為背景,才能寫出他們的苦,這些文學大都表現人在自然和傳統里面的失敗或者胜利。也有部份作家吸收了一些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以後,重新挖掘個人的生命意義。但有很濃的政治浪漫成份。像賈平凹、張承志、史鐵生、張抗抗、鐵凝、北島等,都是這一類風格的作家。
八十年代,是當代文學的成長期。原因之一是共產党的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部分創作自由環境。之二是大量的西方翻譯作品公開發行。八十年代是知青文學和未去插隊的青年一代的試驗性文學和模仿的混雜階段。由于看了同樣的翻譯作品,吸收進去的技巧也都一樣。但每人的性格、智慧和年齡大小不同,寫出的作品還顯得百花齊放。复制卡夫卡、博爾赫斯、海明威、福克納等是普遍現象。成名的作家是因為像馬爾克斯而受到尊敬。馬原以像博爾赫斯被捧為大師、莫言以中國的福克納成了專業作家。老的作家己經沒有能力變化了,只有王蒙還努力地吸了一點喬依斯的意識流。但由于內心的雙重性格不敢太坦蕩,意識流是刻意組織的,讀起來很難受。吸收多的是知識青年一代。由於他們的青春期被党挪用了,現在有了知識,又正處在求知欲很強的年令,大气晚成的壓力很大。但是,他們寫出的作品有太多的仿造感。沒插隊的青年一代吸收西方文化比較正常。他們算是在紅旗下長大,文革中的年令也很小,對毛澤東不恐懼也不崇拜。他們基本上按自己的性格發展起來。
改革開放在八十年代開始時,以解放思想、開放經濟為宗旨。但帶來的思想開放使共產党始料未及。社會環境的多元化很快引起了文學的多元化。因此,左派作家借共產党的招牌和開放帶來的社會失控與混亂,發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染”運動,但己經晚了。社會就像煮了半熟的雞蛋不能再复原一樣。青年作家吸收了個人意識和創作自由的思想,己經不能再回到共產意識的時代。文學題材也由農村轉入他們生活的城市,也開始詢問個人的生存意義。也在這個過渡期,共產党很快釆取了招降納叛政策,開始設立專業作家的職位,使作家進入体制內,形成生死與共的合作關系。一方面是經濟商業的開放帶來的貧富差距,使靠寫作為生的作家面臨貧窮。一方面又給專業作家特殊的生活保障和發展机會。至此,中國作家相繼投入党的怀抱,成了社會主義的作家,在党的体制里叫國家干部。分廳級、省級、市級不等。工資待遇也分等級。他們的作品也揭露落後愚昧,批評時弊和貪官污吏,也寫生不逢時和被商業金錢隔了代的失落感。但躲開了描寫自己生存的精神束縛。作家滿意,党也滿意,一拍即合。模糊了作家與社會以及個人的真實處境。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當高行健獲了諾貝爾獎時,他們的叫罵聲和共產党一個樣。
中國作家由制度的受害者己經變成了制度的受益者,而且有了被執政者承認了的成就感。特別是作品被譯成外語發行,更增加了他們的驕傲。更被他們理解為從中國文壇走向了國際文壇。張顯亮干脆給自己開辦了博物館。模仿毛澤東式的樹碑立傳;從童年由媽媽抱著,少年手握大鋤,直到玻璃框里鑲著二十一個國家介紹他的報紙文章雜誌。証實著專制社會也有了國際作家的存在。他們拿出印有社會主義一級作家的名片,臉不紅心不跳。顯然以在此制度中當作家為榮譽。
這就是權力的威力,它使人怀疑當時作家們反叛專制,原因不過是因為党和政府視了他們而己。中國文化里的“模糊”觀念和傳統,己經成了作家們運用自如的做人方式。
目前,九十年代的作家群,是專業作家與商業流行作家的混合体,這也正是今天中國社會的標准產品。他們的語言缺少顛覆性,語境又抽离了時代時間。它在政治上失去了批判現實的發言權,在生活地位上卻增加了保障。加上文學的概念本來就高于政治,便含糊了在极權的社會,對殘忍和人的尊嚴視而不見,是否具備作家起碼的職業道德問題。嚴肅的文學雖然高于政治,但沒有排除政治。特別是在政治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社會,純文學性是不會存在的。說實話還是作家應該具備的良知。但是,逍遙狀態是中國的傳統意識,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通病。寫自娛和含混人生價值的打油詩,從郭沬若到舒婷就一直沒斷過。作家里面從巴金、到王蒙,也是靠寫些不痛不養的散文隨筆之類的文章活在世上。從未嚴酷地面對自己思想的境界。
我相信共產党垮台之後,中國所有的作家都會說:那時,我們不能那么寫,不然就會失去現有的這點創作自由。或者說:我們己經在作品里表達了人的價值,暗示了專制對人民的壓迫。他們一定會這麼說。問題是,誰教他們靠暗示創作。這群既得利益者們並不都了解作家的職業性質。他們大多數並不明白,作家只能是在精神里展現個人最敏銳的心靈。人格與性格只有在真誠中表露,才可能是完美的文學。不然只是流行一時的宣傳作品。這種虛假的文學,除了可以驗証政治竟可以這麼迫害了一個作家,別的價值沒有。高行健早預見了這一點才流亡法國。也如他說的:真實是文學的倫理。
在中國,作家以為提出公開的政治或人道的建議不在自已的職業范內。忘記了作家的職業就是精神思想的關怀。竟以數學家或經濟學家的職業性質活著。----他們除了有對人和時代沖撞的感受,又可以寫成文字,其它方面應該一無所長。兩面三道、進退自如、能文能商和靠鉆營人事關系而於一身,也是中國作家所獨有的。
社會主義文學是虛假的。那里找不到個人與現代社會的生存狀態。他們寫過去,也幫執政党寫改革開放的成就,也寫社會開放的弊端、貪污腐化和玩乎職守。這些作家又是党的情報員,寫些膚淺的批評是幫助党改正錯誤。看見了他們的“政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便痛訴人性的軟弱,希望他們的共產社會東山再起。他們的工作是使党和政府漸趨完善,繁榮社會主義文藝思想,使之更上一層樓。他們寫歷史的教訓,使党警惕別犯重复的錯誤,引以為戒,也等於在幫助党整理過去對手的罪行記錄。這些題材的作品,幾乎全部是社會主義文學的經典,都獲了獎。也都被漢學家們誤譯為:捍衛了人性的尊嚴,揭露了獨裁統治的作品來出版。在西方便漸漸被誤解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特征。
中國作家的特點還包括:他們可以在公民身份被貶低的情況下寫作,因為只要不太触及政府的政策,便可從不自由進入自由----即進入統制階層內部,成為明哲保身的寄生虫,倒是用行為驗証了社會的集体無意識和麻木。他們也不需要認為寫作是表達生活在世的真理,揭示現存社會的恐懼與不幸。對貶低了人的地位,甚至號召為他人服務,這種缺乏道德的政府,也不表示個人的態度。如果你問作家們相不相信共產党?至今還沒有一個中國作家能正常地表示:“我不相信共產党”。或者:“我相信共產党”。
他們會躲開題目說:我對自己和作品是忠實的。
共產党社會培養了大批在文字內部玩文學游戲的高手,這也說明了社會主義作家的共同點。當代文學一方面滑向過去時態,一方面是個人的失語。如王蒙<失態的季節>、陳染<與往事干杯>,賈平凹<廢都>等等,都是在精神上自嘲和自戀的作品。像年青作家王朔、韓東、朱文、余華、池莉等更是語言的失態,缺乏起碼的克制能力。
目前,商業經濟或者足球文化覆蓋人文價值觀的時代潮流,正好配合了中國專制制度的需要。文明的意義被換成了不要反對和批評政府。做好自己,少管別人的事。而這一點正好又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份。但是,在政治法律甚至基本個人權利還不具備的制度下,政府和作家的這種虛假文明的說法,也正是知識份子最不誠實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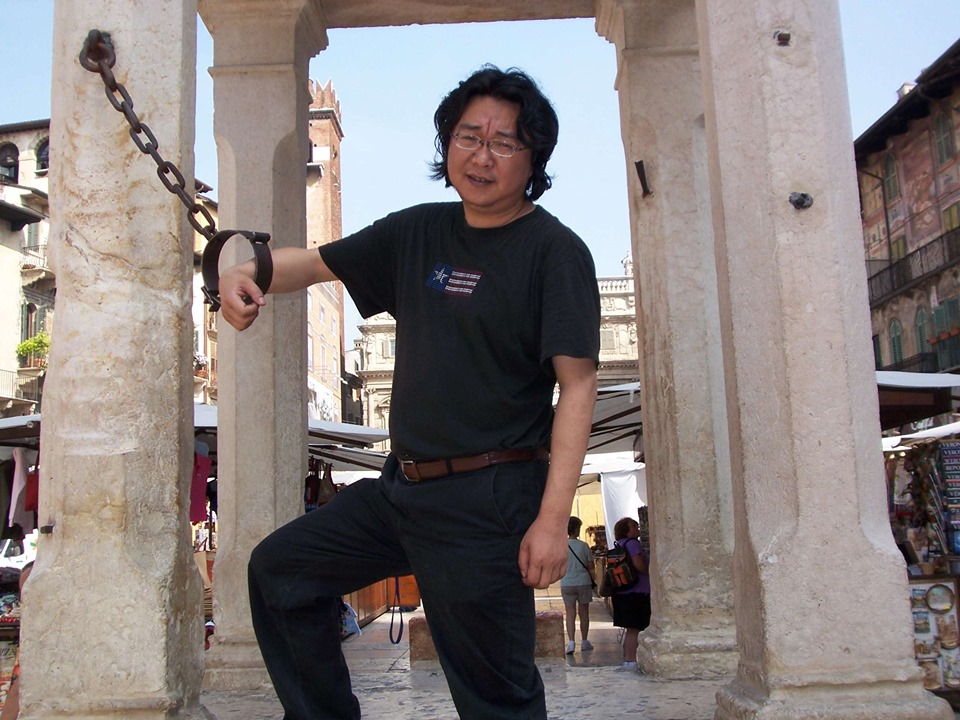
正像台灣八十年代消解權威意識,反諷正統的那批作家一樣。中國作家從反叛正統和傳統禁錮,進而開始反感思想道德的說教。他們發現了自嘲能代替清高的人生之道。阿城、于華等都說寫小說是為了換錢抽煙。像蘇童由先鋒文學演化到流行文學,也說明了中國作家的身份轉換和社會意識的自保,缺乏了對現實的批判性。
奇怪的是,中國所謂的先鋒作家並不帶有反叛意識,而是正統的主流作家。與先鋒的顛覆意指正相反。他們幾乎都愛好古典音樂 [就是歐洲出租司机們听的]。都為家庭生活條件改善,而努力工作 [就是西方保守人士的生活追求]。而寫的作品根本沒什么顛復性,像風油精,隨便在皮膚上擦,舒服一陣就完了。中國一直有借古喻今,指雞罵狗的傳統,正好都遺傳在身体里,提筆表達就是,又和執政者要求的儒家忠孝合拍。這些搔養文學現在從老作家到先鋒作家都一齊掄。
在西方文明社會,談道德真理,基本上是常去教堂的老人。但在中國的共產党社會,作家本來是唯一能用筆說實話的人。他們不是非要去捍衛什么,而是對生存環境表達人的起碼的要求。還應該對社會的不文明,表達他們的看法。這是不同的時代時間,沒有辦法。在极權社會,作家的壓力應該是最大的,而不是魏京生、王丹和吾爾開希這些熱血青年。沒感覺到壓力的作家心靈是麻木的。逍遙可以保護身体和家人的物質生活,但保護不了做人的尊嚴。文學是建立在個人和社會價值之中的,是對反人性的事物有憎惡感的。這不是過問政治,是維護自己的自尊。
中國當代文學的時代背景和作家群体的大概輪廓是這麼。從這些不同的年代和年令的層次看,當代文學的特征又可以分為:
A. 社會主義文學
B. 商業流行文學
C. 嚴肅文學
這三種文學形式並存,而且混雜在作品之中。
在中國公開發行的作品主要是社會主義文學。它的特點是含糊不清。婦女私生活、性變態、公安文學、國共內幕、縣志文學、節約用電、反貪、特區巨變等等,什么都寫。但看不到作家和現實之間的真實。這些作品和各種流派,也會象蘇聯和捷克當時社會上的文學發行物一樣,隨著社會主義垮台,也就不再有人問津了。那時,作家的生活條件和背景也和今天的中國一樣。捷克在六十年代甚至還有發行上万份的地下刊物。但是,缺乏創造力是所有社會主義文學的通病。這些作品具有可消費的,可宣傳教育的和己被政党審查通過了的特點。也一定缺少了個人思想的風釆。
被共產党禁止的作品,可能是當代嚴肅文學的組成部份。因為它可能代表的是不被社會主義認同。如《羊的門》、《國畫》等小說對共產党內腐敗又專權的描寫。另一少部份作品在嚴肅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之間,有待沉澱觀察。社會主義文學在東德和蘇聯,都隨著變革的社會被陶汰了,中國也逃避不了。用經濟意識來悄悄改變人文意識,是弱智政府的無能表現,也救不了專制制度。我也不相信社會主義能產生有思想的文學作品。甚至反叛它都可能損失掉自身的文學性。專制只能把作家的人格變形,從而使作品媚俗,或者精神自瀉。在一個沒有新聞出版自由的社會,作品能公開發行而自豪,結論只能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中國作家從未討論和介紹反對者的作品。不是執政者在反對,是作家們骨子里對自己那點臨時地位的保護。這一點不同別的社會主義文學界。在捷克和蘇聯,社會環境比今天的中國嚴酷,作家們還在討論介紹己經流亡的作家作品。而中國的文學界恨不得流亡作家和文學都消失,以証明他們的存在方式是對的。
當然,流亡作家离開中國之後也很少寫作了。大多數作家和詩人活在去演說的旅途上。我也沒想到演說竟然成了作家的職業。中國有全國作家代表大會,西方也有各種大會小會,他們像討論手工縫制皮鞋似的,互相介紹品質和切磋技藝。這些作家不打算做社會的邊沿角色,而是更想代表某歷史的階段人物。這從名人北島寫的那些無聊的散文中可見其貌。
當然,判斷的失誤總是還包括:反抗對個人精神壓迫的作品,雖然可以進入被禁止發行的書單,也可能不是有價值的嚴肅文學。但對社會主義文學的定義,确能從己經失敗的例子----如東德文學中,尋找經驗。那些党員作家的作品,首先在人格上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專業作家群体也會隨社會變化而起伏分化。然後沉澱出嚴肅的文學。
消解了政治觀念後的流行文學與商業社會價值觀掛鉤,成為現在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像台灣十幾年前的文學界一樣。但中國的社會開放並不等同思想的開放。盡管党在証明一視同仁,作家們在証明仁愛之心。他們又都擠在政府大樓里辦公,都贊成儒道,都是体制的受益者。盡管他們每隔幾年都宣佈一個新的主義,這些文學潮流也沒有离開中共宣傳部的領導。都在党的總頭目江澤民所要求的:要創作鼓舞人心的優秀作品的范圍內。無論流行還是商業化,都沒有大的精神思想與社會的沖突,都是和天時地利協調的農作物,什么气候就只能長什么庄稼。
那麼,出現的問題是以往對中國文學的介紹和翻譯,是否還具有沿續的意義。在翻譯文學作品中,因為太偏重滿足對專制社會的好奇,文學己失去文學性。大概只具有社會學的意義。流亡文學政治化和商業化傾向,也己經証明中國當代文學的幼稚。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其間,《上海寶貝》一下子變成本時代的中國名著,就是個典型案例。由老右派的訴苦文學,又派生出來的當代婦女訴苦小說,己完全成了西方認同的中國文學品味。按此格式化的發展:她、媽媽、奶奶,三代女人被壓迫,加上歷次的政治運動,換個地名人名就是一本暢銷書。象張戎、露露等女性作家都是迎合了西方人的認同產品,也根本不是文學。她們使中國小說失去語言和精神的獨創性。這也使人怀疑當代文學的特征己內外都被模式化了。創作不是沉思,倒像是天橋上的模特的造作的表演。另外,整体的文學方向离現實的時代時間越來越遠,也就失去了文學的真實了。
社會主義專制在二十世紀的實驗和失敗,表明了它產生不了獨特的精神思想,而文學思想的蒼白正好証實了這一點。它轉換成另類專制當然是進了一步,但离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期許還差很遠。
中國當代文學的特征是帶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出現的,其次是作家各人的風格的獨創性。二十世紀初到現在,現代文學由白話文演化到當代文學,時間還很傖促。由於和西方的社會環境不同,中國作家仍然要面對著社會政治的現實。做人的道德感和作品的風格是互相存在的。以消化和排泄為例來看:在中國說創作自由,是叫你隨便吃,但拉屎要由領導審查批准。中國作家只好在吃的時候,每一口都在考慮出版時能否順利通過。作品明顯地知道自己在刻意做了什么。在台灣和香港可以是完全自由的吃,更可以自己決定何時進廁所。但他們吃和拉的速度太快了點。這種現象全世界都存在著:网络文學、、卡通文學等將成為主流,有独立思想的文学将被移出哲学领域,文学也将快餐化了。

马 建
2025.7.11
2025 年 7 月 13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