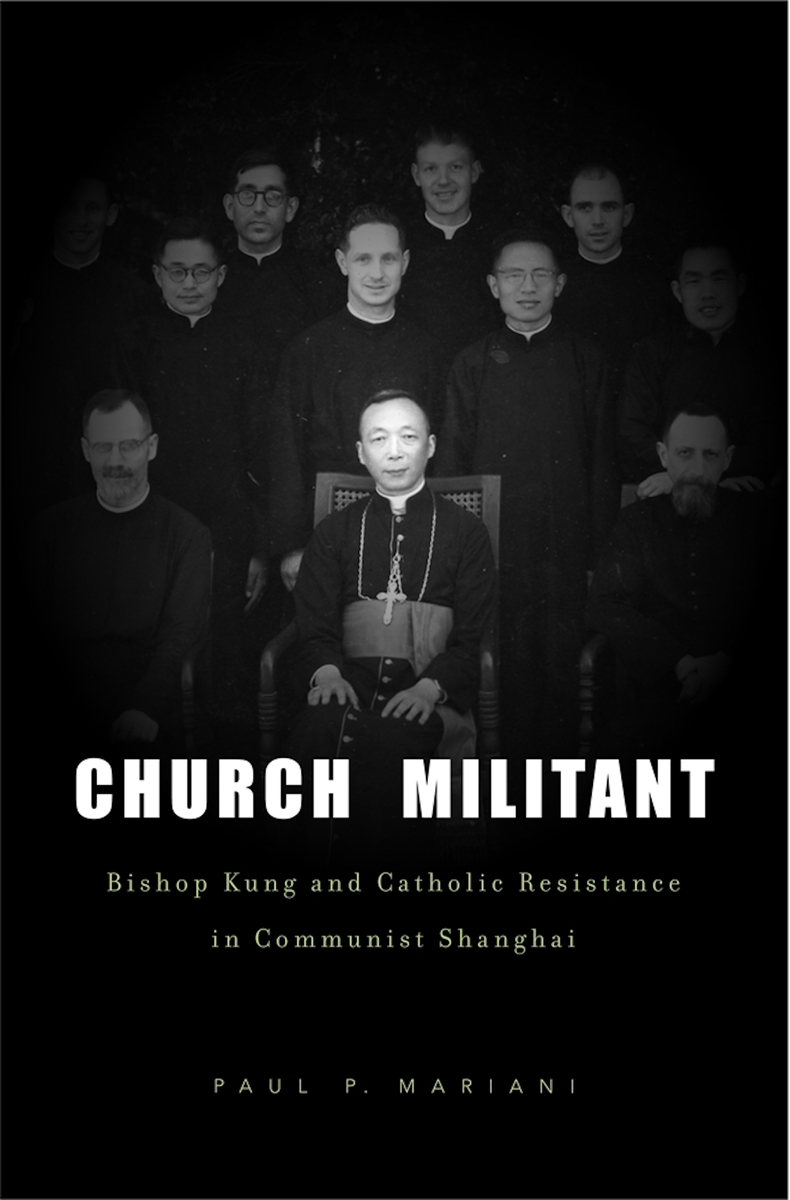
张成信:战斗的教会:一本书里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前后(上)
1955 年 9 月 8 日深夜,上海的天主教会迎来了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当晚,以龚品梅主教为首的数百名神职人员与平信徒领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全市大搜捕中被投入监狱,官方的定性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这一事件,不仅是上海天主教会命运的急剧转折,更象征着一个要求绝对政治效忠的新生政权,与一个坚持普世性信仰忠诚的古老宗教团体之间,一场无可避免的殊死对决已然拉开序幕。这场对决的核心诘问尖锐而古老: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条界线究竟应由谁来划定?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掌握了通往人间天堂的唯一真理时,另一个宣称其信仰指向超验天国的团体,其抵抗的空间何在?其抵抗的形态、策略与代价又为何?Paul P. Mariani 的力作 Church Militant: Bishop Kung and Catholic Resistance in Communist Shanghai,正是迄今为止,对此历史诘问所给出的最为全面、深入且具洞察力的学术回应。
Mariani 此书的问世,为当代中国宗教史,特别是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教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座标。此前,以邢福增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学界多从宏观政策与制度建构的视角,剖析了中共党国体制如何设计并推行其宗教管控的顶层蓝图。这些研究清晰地勾勒出中共在意识形态(无神论)与现实政治(统一战线)的张力之间,逐步建立起一套“计划宗教”体制的宏大历史进程。Mariani 的贡献,正在于他将镜头从北京的决策中枢转移到于上海这一具体而复杂的历史场景。他透过对新近解密的上海市档案馆内部文件以及大量教会文献、口述历史的细致梳理,生动地展示了那套宏观的管控政策,如何在地方层面被演绎为一场充满残酷细节与人性挣扎的具体实践。他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策的颁布,还有政策执行过程中党国机器如何进行情报搜集、群众动员、宣传攻势乃至审讯逼供的精细运作。
另一方面,若将此书与杨奎松等学者对知识份子及特定机构在政权鼎革之际命运的微观叙事并置,其独特性亦跃然纸上。杨奎松近年在台湾发表的论文《燕大挽歌》以悲悯而冷峻的笔触,描绘了以陆志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试图在新政权中寻求生存空间却最终幻灭的悲剧。那是一个关于“顺应”与“改造”的故事。然而,Mariani 笔下的上海天主教会,呈现的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面貌:一个关于“抵抗”的故事。书中的主角——从龚品梅主教到圣母军的青年学生——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妥协的空间极为有限,并因此选择了一条有组织、有策略、有神学思想支撑的抵抗道路。Church Militant 这本书的重大价值,便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迫害与受害”二元叙事,转而深入抵抗行动的内部,细致解剖了这个“战斗的教会”的组织肌理、神学动力及其最终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后果。它让历史中那些模糊的「受害者」面孔变得清晰,让他们的抵抗不再仅仅是消极的承受,而是一场充满能动性的艰苦搏斗。
一、
Mariani 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具体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天主教三角区”(the“Catholic triangle”)。这个以圣伯多禄堂、君王堂和徐家汇耶稣会大院为顶点的区域,集中了上海最重要的天主教学校、修院、堂区与善会组织(p. 23)。作者对徐家汇——这个始于明末徐光启,历经数百年发展而成的“亚洲中心的微型基督王国”(p. 8)——的描述尤为精彩。它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天主教信仰在中国并非无根的浮萍,而已然深度嵌入本地社会肌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Mariani 精准地提炼出上海天主教会力量的两条“血脉”(p. 17)。其一,是植根于本土的“地方亲属网络”。他追溯到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时代,指出上海天主教会在 17 世纪就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本土基础。通过对朱氏、陆氏等天主教大家族的个案分析,作者力证了这些绵延数代的信仰传承,为教会提供了稳定的人力(神职人员)与财力支持,并形成了一张坚韧的社会支持网络(p. 17-19)。这有力地驳斥了中共宣传中将天主教简单化约为纯粹“舶来品”与“帝国主义工具”的刻板印象。其二,则是联通世界的“全球网络”。这种与罗马教廷的“超国家”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资金、人员与神学思想的持续输入,构成了上海教会力量的另一极(p. 20)。正是这两条血脉——一条深植本土,一条联通普世——共同塑造了 1949 年前夜上海天主教会的独特面貌:它既是中国的,又是大公的;它既古老,又充满现代性。
主教、耶稣会士与青年信徒
如果说宏大的历史场景是舞台,那么鲜活的人物则是历史剧的主角。Mariani 此书的另一大叙事魅力,在于他成功地从冰冷的档案与泛黄的故纸堆中,拯救出了一系列有血有肉、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们不再是历史洪流中面目模糊的牺牲品,而是拥有各自信念、恐惧、挣扎与抉择的行动者。
龚品梅主教无疑是全书的灵魂。Mariani 笔下的龚品梅,并非一个天生的政治斗士。他出身于一个融合了儒家传统与法式天主教文化的家庭,既为自己的国籍感到自豪,又对教会的普世性忠诚毫不动摇(p. 29)。作者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细节:1950 年被任命为主教后,上海的教友们不再称他为“the bishop”,而是亲切地称为“our bishop”(p. 43)。这个称谓的转变,象征着在“外国传教士”即将退场的历史时刻,一位本土主教所承载的巨大期望。Mariani 通过龚品梅主教在关键时刻(如 11 月 29 日与潘汉年副市长的会面)的发言,以及他发布的一系列牧函,塑造了一个在神学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在政治风暴中努力寻求保护羊群之道的坚毅牧者形象。
张伯达神父,这位毕业于索邦大学的耶稣会士,圣依纳爵公学的校长,是“中间立场”的提出者——即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在次要问题上退让,但在信仰核心问题上坚守不移(p. 38)。更重要的是,他是天主教青年运动的灵魂人物,是他一手策划并组织了“要理小组”(catechism groups)和“特别战斗员”(special militants)这些高度组织化的秘密团体(p. 52-53, 62-65)。Mariani 准确地指出,正是张伯达的远见与组织才能,为上海教会的抵抗提供了最富活力的骨干力量。他最终在狱中殉道(p. 87-88),也成为了整个抵抗运动中最具感召力的象征。
耶稣会会长格寿平神父(Father Fernand Lacretelle)则是书中最为复杂和悲剧性的人物。作为代表罗马强硬反共路线的“顽固派”(p. 37),他最初是抵抗意志的象征。然而正是他,在经历了长达 550 个小时的残酷审讯与精神折磨后,写下了长达 769 页的“悔过书”,并亲口录音,承认龚品梅是一个“帝国主义者”(p. 157-161)。Mariani 对此的处理极为审慎而充满同情,他没有简单地将其定性为“叛徒”,而是细致地分析了极权机器如何通过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来击垮一个人的意志。格寿平的崩溃,成为瓦解教会团结最致命的一击,其个人悲剧也因此折射出整个时代更为深重的悲剧性。
最后,也是最令人动容的一笔,是 Mariani 对“天主教青年团”(Catholic Youth)这一群体的描绘。他们是圣母军(Legion of Mary)和圣母会(Marian Sodalities)的核心成员,是这场“战斗”的“脊梁”(p. 47)。在 Mariani 的笔下,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被煽动的“羔羊”,而是信仰坚定、组织严密、充满牺牲精神的年轻战士。无论是公开的游行示威,还是秘密的要理学习;无论是在街头与“进步青年”辩论,还是在狱中面对审讯,他们都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与成熟。正是透过对这些普通青年的书写,Mariani 将这场抵抗从少数精英的对抗,还原为一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信仰保卫战,赋予了这段历史以深厚的社会史意涵。
从“画线”到“全面突击”
Mariani 的叙事结构清晰而富有逻辑,他以“划清界线”、“定点打击”和“全面突击”等章节标题,精准地勾勒出中共与上海天主教会之间冲突逐步升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 年至 1950 年中的“不安的和平”(p. 26)。此时,新政权立足未稳,仍需采用“统一战线”策略(p. 31),而教会内部则在“强硬”、“妥协”与“中间”三条路线之间摇摆(p. 37-38)。Mariani 通过对当时教会领袖信件的分析,敏锐地捕捉到了双方都在试探彼此底线的微妙状态。中共通过税收、学制改革等方式进行“三面施压”(p. 32),而教会则试图在服从新政权与保持信仰完整性之间寻找平衡。这一阶段的叙述,为后续冲突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是 1950 年中至 1953 年中,以韩战爆发为催化剂的“定点打击”。Mariani 清晰地指出,中共的策略并非直接取缔教会,而是通过打击其所谓的“帝国主义联系”,将其“肢解”并改造成一个驯服的“爱国”团体。这一策略的执行有着明确的路线图。Mariani 通过对《解放日报》等官方文献的解读,还原了这场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序列:首先,驱逐代表教宗的黎培理公使(Archbishop Riberi),斩断教会的“大脑”(p. 69);其次,查封作为主教团联络与出版中枢的“公教进行会”(Catholic Central Bureau, CCB),摧毁其“神经系统”(p. 71);最后,取缔拥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平信徒组织“圣母军”,砍断其“手足”(p. 75)。Mariani 对这一系列行动的细致叙述,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党国机器在瓦解一个社会组织时的冷酷效率与系统性。
第三阶段,则是以 1955 年 9 月 8 日大逮捕为高潮的“全面突击”。如果说之前的打击尚且披着“反帝”的外衣,那么这一次则是图穷匕见,直接指向以上海主教为核心的整个教区领导层。Mariani 对此夜的描述极具画面感:警笛划破夜空,红色的警车(被市民称为“大红包”)穿梭于大街小巷,从主教座堂到普通信徒的家庭,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在同一时刻收紧(p. 1, 148-150)。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群众控诉大会、分化瓦解的“学习班”以及最终在赛马场举行的万人公审大会。Mariani 通过对这些场景的重构,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国家暴力与群众狂热相结合的恐怖氛围之中。这场“突击”的最终目的,正如 Mariani 所引述的党内文件所言,是要“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隐藏在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及其领袖龚品梅”(p. 151)。

二、
如果说 Mariani 的历史叙事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上海天主教会面对压迫时的坚韧抵抗,那么这部著作更为深刻的贡献,则在于它掀开了那台巨大国家机器的帷幕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其内部运作的精密与冷酷。本书的巨大价值,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对新近开放的上海市档案馆中一批标示为“机密”的党内文件的开创性运用。这些来自宗教事务局和宣传部门的文件,与教会方面的史料形成了完美的互证与对话。我们可以从 Mariani 提供的丰富细节中,提炼出中共早期党国体制在处理一个“棘手”宗教团体时,其管控策略的完整逻辑链条。这套策略融合了成熟的统战技巧、严密的组织手段与毫不留情的国家暴力,旨在将一个拥有普世忠诚的独立社群,彻底改造为服务于国家意志的驯服工具。
“分而治之”:中共宗教政策的逻辑
中共处理宗教问题的总方针,从其革命时代起便已确立,即“团结与斗争”的辩证统一。他依据一份写于 1950 年夏天的机密文件《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揭示了中共在面对上海教会时,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极为清晰的“分而治之”策略(p. 39)。
首先,文件明确指示,斗争的核心目标并非笼统的“教会”或“天主教徒”,而是要精确打击“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少数分子”,同时“团结大多数信教群众”(p. 40)。这套话语体系成功地将一个信仰问题(宗教忠诚)转化为一个政治问题(爱国与否),从而为后续的镇压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外衣。党国机器成为了“爱国主义”的唯一阐释者和裁判者。Mariani 敏锐地指出,对天主教会而言,这种切割是致命的,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教会作为“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來”的普世本质。中共的策略,正是在教会的“大公性”(catholicity)上,楔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楔子(p. 56)。
单纯的外部打压容易激起同仇敌忾,而从内部攻破堡垒则事半功倍。Mariani 详尽地描述了中共如何物色并扶植教会内部的“爱国”、“进步”力量,以对抗以龚品梅主教为首的“反动”领导层。从早期的胡文耀到后来的金鲁贤,这些人物在官方叙事中被塑造为“爱国教徒”的典范。他们被赋予资源,组织平行的“三自革新运动”,并最终在 1955 年后成为官方认可的“爱国会”的领导核心。通过这些内部代理人,党国得以将自己的意志延伸到教会组织内部,实现对其的间接控制。这套“以教制教”的策略,其后遗症绵延至今,成为中国天主教会内部长期分裂的根源。
最后,在手段上采取行政“绞杀”。除了政治分化,Mariani 还揭示了新政权如何运用税收、教育、人员流动管制等一系列非宗教的行政手段,对教会的生存空间进行系统性压缩,他称之为“三面夹攻”(p. 32)。沉重的税收(p. 33)耗尽了教会的财力;强制性的课程改革与政治干部进驻学校,则夺走了教会对年轻一代进行信仰教育的核心阵地(p. 34-35);而对外国传教士活动范围的限制,则切断了他们与地方社区的联系,并加重了中国籍神父的牧灵负担(p. 36-37)。这一系列看似“中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其叠加效应却是致命的。它使得天主教会这一庞大的社会实体,在尚未遭到直接政治打击之前,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已被大幅削弱,陷入了“温水煮青蛙”的困境。
宣传、审讯与“再教育”
宣传战是第一步,旨在抢占道德与舆论的制高点,其核心手法,是将教会内部的信仰坚守,重新定义为一系列政治罪名。例如,圣母军原本是一个以祈祷和传教为宗旨的平信徒善会,在官方宣传中,却被描绘成一个“搞反动活动的组织”,其创始人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守护者”(p. 77)。对黎培理公使的攻击,则将其梵蒂冈外交官的身份,扭曲为“美帝国主义的间谍”(p. 58)。这些宣传攻势不仅充斥着报纸版面,还配合着展览、群众大会等形式,营造出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后续的逮捕与镇压铺平道路。
审讯与逼供则是将宣传“坐实”的关键环节。书中关于格寿平神父、麦卡锡神父(Charles McCarthy)等人狱中经历的描述,是全书最令人震撼的部分之一。Mariani 指出,中共的审讯体系,并非单纯追求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一套旨在摧毁个人意志与尊严的心理战术。长时间的疲劳审讯、剥夺睡眠、精神羞辱,以及更为阴险的,利用伪造的“证据”(如同伴已经招供的假象)来制造孤立与绝望感(p. 160)。格寿平神父的案例尤为典型:这位意志坚定的耶稣会会长,在经历了长达十三个月、累计 550 小时的审讯后,精神与肉体彻底崩溃。他那份长达 769 页的“悔过书”,以及被迫录制的录音带,随即被当局作为最强大的武器,用于瓦解其他神职人员的抵抗意志(p. 162-163)。“你们的领袖都已经招了”,这句话的杀伤力,远胜于任何物理酷刑。它从内部撕裂了抵抗团体最宝贵的资产——信任。
“再教育”与“思想改造”则是针对更广泛群体的精神收编。在 1955 年大逮捕之后,五十多位未被立即投入重刑监狱的神父被集中起来,参加长达数周的“学习班”(p. 152)。Mariani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学习班”的场景:昔日备受尊敬的神父们,被迫聆听“进步分子”的控诉,一遍遍学习批判教会“罪行”的报纸文章,并被要求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其目的在于彻底剥离他们作为神职人员的尊严与权威,使其从心理上接受党国的话语体系。对于青年学生,这套改造体系同样有效。Mariani 记录了中共干部如何精准地抓住年轻人的弱点,他们对父母的孝顺、对学业与前途的担忧,迫使他们与教会划清界限(p. 154)。
韩战与镇反运动的催化作用
为何中共对上海天主教会的政策,在短短几年内,从相对谨慎的“团结、教育、改造”,急剧转变为以彻底摧毁为目标的“全面进攻”?Mariani 指出,正是两场几乎同时爆发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构成了上海天主教会命运急转直下的催化剂。第一个催化剂是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Mariani 论证道,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气候。原本作为“统战对象”的社会团体,一旦与“美帝国主义”发生任何关联,便立刻成为潜在的“第五纵队”(p. 54-55)。上海天主教会不幸地同时具备了两个“原罪”:其一,它与梵蒂冈的联系,被直接等同于与西方世界的政治联系;其二,教区内存在大量的美籍、法籍传教士,他们一夜之间从“友人”变成了“敌国侨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狂热宣传下,“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成为最便利的动员靶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三自革新运动”被迅速政治化,从一个教会内部的改革议题,演变为一场要求与“帝国主义”彻底割席的政治效忠运动。
第二个是 1951 年和 1955 年先后发动的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Mariani 详尽描述了 1951 年 4 月上海“镇反”高潮时的恐怖气氛:红色的警车呼啸而过,大规模的公开处决在赛马场举行,整个城市笼罩在血腥的恐惧之中(p. 61)。正是在这股疾风暴雨中,对教会学校的接管、对张伯达神父等人的首次逮捕得以顺利推行。而 1955 年的第二次“镇反”运动,则为最终解决“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提供了完美的政治契机与法律依据。Mariani 引用党内文件指出,对龚品梅集团的打击,被明确定义为“镇反运动”在上海天主教界内部的延伸(p. 146)。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