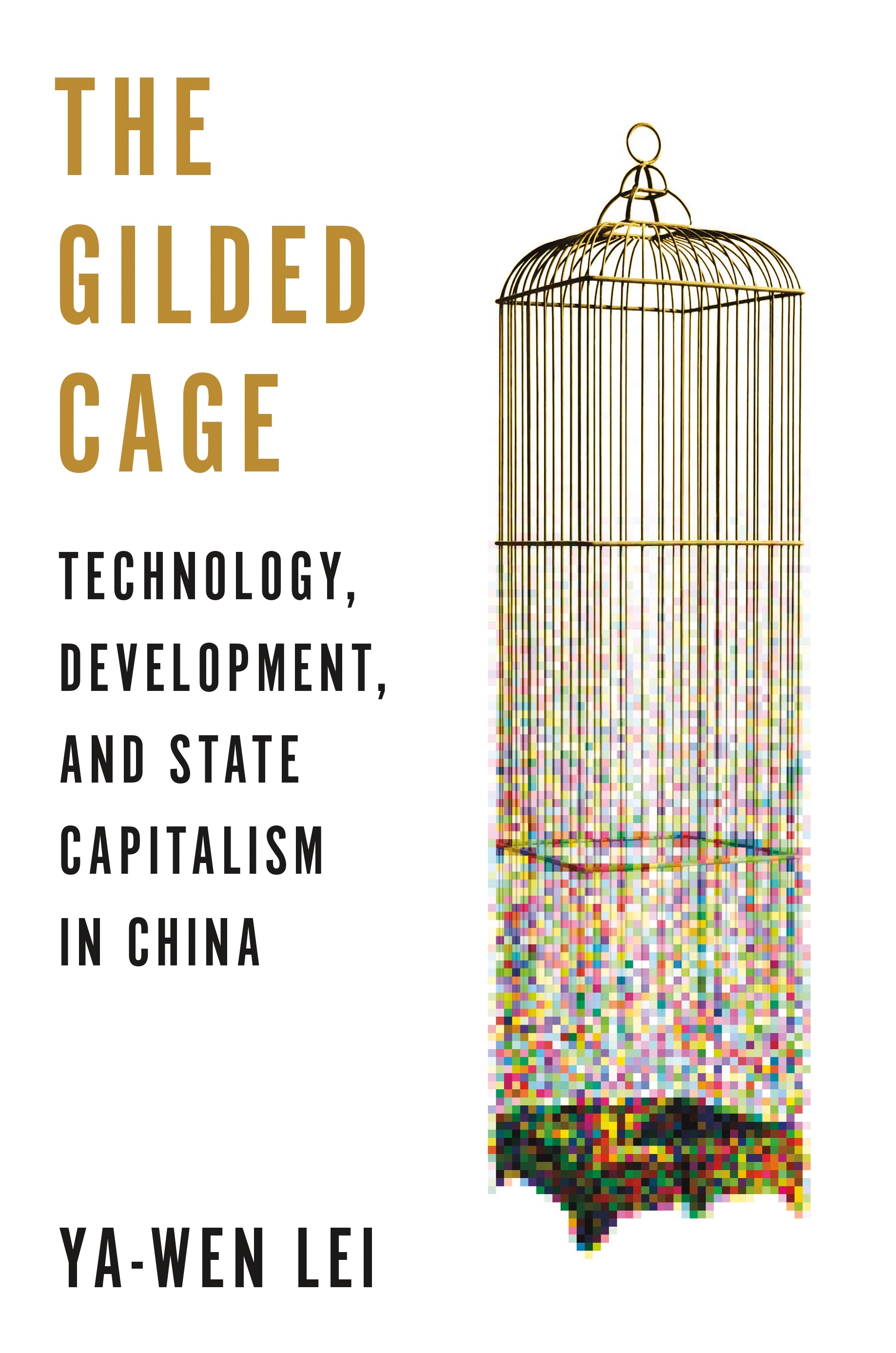
镜空:“中国式现代化”还是“通往奴役之路”?评雷雅雯“The Gilded C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下)
三、
那么,“笼子”腾出来了,总得有“新鸟”进来吧?这些“新鸟”又是何方神圣,它们和“笼子”的关系,又是怎样一番光景?雷雅雯在书中花了大量笔墨,细致剖析了以平台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新鸟”的崛起,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这些“新鸟”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单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怕是没这个魔力。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这些名字,如今在全球都如雷贯耳。它们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同行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路。这背后,当然有企业家精神,有技术创新,但更重要的,是雷雅雯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国家与科技巨头之间的一种“非对称共生”(asymmetrically symbiotic)关系。
这个词有点拗口,但说白了,就是一种互相需要、互相利用,但地位并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先看国家是怎么“养鸟”的。
第一,也是最根本的,是国家为这些科技“新鸟”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温室”。这个温室,就是臭名昭著的“防火长城”。我们过去总从政治角度看这堵墙,觉得它是言论管制的工具。这当然没错。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堵墙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它把谷歌、Facebook、Twitter 这些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挡在了国门之外,为本土的互联网企业圈出了一片广阔的、没有天敌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能否如此顺畅地崛起,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可以说,这堵墙,就是“新鸟”们赖以生存的“笼子”的边界。
第二,是“容忍”的智慧。在这些“新鸟”的早期发展阶段,国家采取了一种在雷雅雯看来是“宽容的监管姿态”(tolerant regulatory approach)。很多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但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做法,都得到了默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中国的法律,对某些敏感行业的外资准入是有严格限制的,互联网就属于这一类。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一开始没钱没技术,最需要的就是海外的风险投资。怎么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在开曼群岛等地注册离岸公司,再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协议来控制国内的运营实体,这些企业成功地绕开了监管,拿到了宝贵的美元基金,得以在美国上市。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但监管部门对此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水至清则无鱼。没有这种变通,就没有后来这些科技巨头的茁壮成长。这种选择性的“容忍”,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策支持。
第三,是实打实的“喂养”。除了提供保护和容忍,国家还直接下场,为“新鸟”的成长添砖加瓦。从“互联网+”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种国家战略和政策口号,都把互联网和平台经济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科技巨头的创始人,也纷纷被戴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帽子,成了体制内的座上宾。这不仅给了他们政治上的光环和安全感,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资源。政府项目的外包、数据资源的开放,都为它们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那么,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养鸟”,图的是什么呢?雷雅雯的分析同样一针见血。科技巨头们,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国家实现其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它们一方面创造了海量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从“旧鸟”企业失业的工人,扮演了社会“稳定器”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们凭借其技术和平台优势,成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延伸和渗透的“毛细血管”。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极短时间内,几家科技公司就开发出覆盖全国的健康码系统,成了对十几亿人进行精细化管控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界限变得模糊,平台成了“准政府”机构,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商关系,国家不再仅仅是监管者,企业也不再仅仅是市场主体,二者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捆绑。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双赢”的故事。国家实现了发展和稳定,企业获得了市场和利润。但雷雅雯提醒我们,事情还有另一面。这些被国家精心饲养和赋能的“新鸟”,在羽翼丰满之后,它们自己也开始筑起了新的“笼子”,一个“笼中之笼”,雷雅雯总结为“技术和法律工具”(technical and legal instruments)。“技术工具”,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的算法。无论是外卖平台的派单系统,还是电商平台的推荐引擎,其背后都是一套精密的算法。这套算法,以“效率最优化”为最高目标,对平台上的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骑手、商家还是消费者——进行着无时无刻的测量、评判和调度。雷雅雯对平台骑手工作状态的描述,揭示了算法之下的冷酷。骑手们看似是“自由”的个体户,可以“自由”地选择接单时间,但实际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平台的严密监控之下。送餐的时间被系统精确到秒,路线被规划得不差毫厘,顾客的一个差评就可能让他们一天的辛苦付诸东流。他们不是被工头管理,而是被冰冷的算法所统治。这是一种更隐蔽、更高效,也更让人难以反抗的控制。
“法律工具”又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在注册 APP 时,都不得不点“同意”的那些长篇大论的用户协议和平台规则。这些由平台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赋予了平台巨大的、不对等的权力。它可以随时修改规则,可以对违规者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单方面终止服务。在这种关系中,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和商家,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要么接受,要么退出。
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吊诡的图景:这些科技巨头,本身是国家这个大“笼子”里的“鸟”,它们仰仗着笼子的保护和喂养;但同时,它们又在自己的领地里,建造了无数个小“笼子”,把亿万劳动者、商家和用户变成了它们“镀金鸟笼”里的新居民。它们既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又在自己的“数字王国”里行使着类似国家的权力。它们既是被规训者,又是规训者。这种双重身份,是理解平台经济中各种矛盾的关键。
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非对称共生”关系,本身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问题在于,当“鸟”长得太大、太壮,翅膀太硬的时候,它会不会开始觉得“笼子”有点小,甚至想挑战“笼子”本身?雷雅雯在书的后半部分,浓墨重彩地分析了 2020 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发起的猛烈的监管风暴。这场风暴,以叫停蚂蚁集团上市为标志,以反垄断、数据安全、算法规制为主要内容,让全世界都为之震动。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政府会对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模范生”下此重手?是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那番演讲惹怒了中共高层吗?
把原因归结于一次偶然的言论,显然是看轻了这背后的深刻逻辑。雷雅雯的分析,将其归结为这套“技术 - 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的必然爆发。当科技巨头的力量大到一定程度,开始触及国家的核心权力领域时,冲突就不可避免。
首先是金融。蚂蚁集团的崛起,本质上是在国家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以数据和信用为基础的平行金融帝国。它绕开了传统银行的资本金约束,直接连接着亿万储户和借款人。这在主政者看来,无疑是在挑战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根本垄断,是在制造系统性金融风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第二,平台巨头们通过其业务,掌握了比任何政府部门都更全面、更细致的国民数据。这些数据,既是巨大的商业资产,更是潜在的国家安全资源。当滴滴出行不顾监管部门的劝阻,执意赴美上市时,在中共主政者看来,这无异于将核心的国家数据资产置于他国司法管辖的风险之下。这是中共国家安全这根“红线”所绝不能容忍的。
最后是舆论。平台不仅是交易的场所,也是信息的入口和舆论的广场。它们通过算法推荐,深刻地影响着公众看什么、信什么。这种塑造社会共识的权力,是任何一个威权体制都必然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当平台的舆论影响力大到足以和官方分庭抗礼时,收紧缰绳就成了必然之举。
所以,这场监管风暴,并非心血来潮,而是这套体制的逻辑必然。雷雅雯将其称为“重塑鸟笼”(Remaking the Cage)。它传递了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在这个国家,资本,哪怕是最高科技的“新鸟”资本,也永远只能是权力的工具,而绝不能成为与权力平起平坐的伙伴,更不用说挑战权力本身。当“鸟”威胁到“笼子”的权威时,笼子的主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剪掉它的翅膀,收紧它的活动空间。
这场风暴,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雷雅雯“非对称共生”这个概念的含义。“共生”是真的,但“非对称”是更根本的。在这段关系中,国家始终是那个拥有最终解释权和最终裁决权的一方。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放水养鱼,也可以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关门打狗。企业家们所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本质上是一种“特许经营权”,随时可以被收回。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在上一部分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安全的私有产权。一切产权,最终都是国家权力下的蛋。这,或许就是这个“镀金鸟笼”最根本的、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真相。

四、
那么,生活在这座日益精致、金光闪闪的笼子里的“笼中人”,他们的日子过得究竟怎么样?雷雅雯这本书最精彩、也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在我看来,就是她对“编码精英”(coding elite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件工程师、程序员——这个群体的深入描摹。
这个群体,按理说是这个“镀金时代”最令人艳羡的天之骄子。他们学历高、智商高、收入高,出入于城市最核心地段的现代化写字楼,被视为“工程师红利”的代表,是驱动中国“技术 - 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这部庞大机器的最关键零件。他们无疑是“新鸟”中的佼佼者,是这镀金鸟笼里最亮丽的风景线。
可是,雷雅雯通过细致的访谈告诉我们,风景线的日子,并不好过。先看他们的工作状态。外人看到的,是他们的高薪和弹性工作制的神话。但身处其中的人都知道,现实是“996”。“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周六天”,这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潜规则,甚至是一种值得炫耀的“奋斗文化”。雷雅雯在书中对这种工作模式的分析,远不止于抱怨工作时间长。她把它看作一套精密的、以绩效考核(KPIs)为核心的控制系统。阿里巴巴著名的“361 考核”(即 30% 优秀,60% 合格,10% 待改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种高压的末位淘汰制下,每个人都像是在一台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上。你不仅要跑,还得比身边的人跑得更快,否则就会被甩下来。加班,不再是简单的“多劳多得”,而成了保住饭碗、争取晋升的“投名状”。
这种高强度的“绩效主义”和“结果导向”,无疑能激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这也是这些科技巨头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秘密武器。但代价是什么?是人的异化。工程师们不再是创造性的劳动者,而更像是一颗颗在系统里高速运转的“螺丝钉”,他们的工作被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 KPI,他们的价值被简化为一个个冰冷的绩效得分。一位受访者形容自己是“人肉电池”,用完即弃。这个比喻,残酷,却也精准。
如果说工作上的“敲骨吸髓”还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那么生活中的巨大压力,则是另一半,甚至更沉重的一半。雷雅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这些“编码精英”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社会再生产”的难题。这个社会学术语,说白了,就是成家立业、安居生子这些最基本的人生需求。按理说,他们收入那么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不难吧?可现实偏偏就是这么吊诡。他们的高收入,在更高得离谱的资产价格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一套能让孩子上个好学校的“学区房”,动辄上千万。这笔钱,对绝大多数工程师来说,即便掏空“六个钱包”,也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我们第一部分谈到,地方政府搞“技术转向”,其财政基础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土地财政”。也就是说,正是这个推高了地价和房价的制度,为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基础建设;但反过来,也正是这个制度,使得在这个产业中工作的精英们,买不起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这座城市的房子。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却分享不到城市化最丰厚的果实——资产增值。他们成了高收入的“无产者”,一群漂泊在自己参与建造的繁华都市里的“伪中产”。
雷雅雯在书中对北京海淀区的描绘,把这种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那里既是中国顶尖高校和科技公司的聚集地,也拥有全国最昂贵的学区房。工程师们为了给孩子一张进入“海淀模式”的入场券,不得不投入一场比“996”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的教育“军备竞赛”。他们的焦虑,不再是简单的职业发展,而是深刻的阶层滑落的恐惧。一位受访者说得好:“我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继续像我们这样努力工作。”这句话的背后,是深深的幻灭感。
面对这种普遍的困境,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雷雅雯把这个精英群体进一步细分,画出了几张生动的脸谱,让我们看到了“笼中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类是“奋斗者”。他们大多出身农村或小城镇的工薪家庭,是靠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才实现了阶层跃迁。他们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格言最坚定的信徒。对于“996”,对于高房价,他们虽然也感到疲惫和压力,但内心深处是认同的。他们认为,吃苦是理所应当的,奋斗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径。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崛起紧密相连,觉得自己的“牺牲”是为了“民族复兴”这个更宏大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是这套体制最忠诚、最坚韧的基石。
另一类是“优化者”。他们多半出身于城市中产或以上家庭,从小见多识广,资源更丰富。他们对体制的逻辑看得更透,也更善于利用规则。他们不会死磕在一个地方,而是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看作一场“投资组合”。他们会精算每个选择的“性价比”:哪家公司的“班”加得最有价值,哪家公司的股票期权最诱人,跳槽到哪里能实现收入和生活品质的最大化。他们也抗争,但方式是“用脚投票”。当他们觉得一份工作“不划算”时,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他们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精致的,其目的不是改变规则,而是在现有规则下为自己争取最优解。
还有一类,就是“躺平者”。当“奋斗”的前景变得渺茫,“优化”的空间越来越窄时,一种新的情绪开始蔓延。雷雅雯记录了“996.ICU”这场网络抗议。虽然这场抗议在现实中并未激起太多浪花,但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标志着这个群体内部某种集体性的觉醒。它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工作是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工作?”
近年来流行的“内卷”(involution)和“躺平”(lying flat)等网络热词,更是这种幻灭情绪的集中体现。“内卷”描述的是一种停滞性的、自我消耗式的竞争状态,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但整个系统却原地踏步。“躺平”则是一种消极的、非暴力的不合作。既然游戏规则如此不公,获胜的希望又如此渺茫,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不玩了。我降低欲望,放弃竞争,只求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当一个社会最聪明、最有活力的那群年轻人,开始集体选择“躺平”时,这对于这个号称要“星辰大海”的“镀金鸟笼”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恐怕比任何形式的公开抗议,都更具颠覆性。
这背后,最终还是一个“绩效”与“代价”的权衡问题。毫无疑问,这套“技术 - 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在宏观层面取得了惊人的“绩效”。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平台应用冠绝全球,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也实现了“弯道超车”。这正是“镀金鸟笼”那“镀金”的一面。雷雅雯在访谈中也发现,即便是那些对自身处境多有抱怨的工程师,在谈到国家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时,也常常流露出自豪感。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相信自己的辛苦和牺牲,是“国家发展现阶段不可避免的代价”。
这种将个人牺牲合理化的国家主义叙事,无疑是维持这套高压体制运转的重要润滑剂。但雷雅雯的书,恰恰是要我们追问,这代价,究竟是什么?由谁来承担?它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清晰的。代价,是“旧鸟”们的破产倒闭,是“低端劳工”的被排斥和驱逐,是“编码精英”们的身心俱疲和希望幻灭。代价,是整个社会在“效率”和“优化”的单一价值维度下,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的普遍贬损。在这个体制里,人不再是发展的目的,而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人力资源”或“工具”。当“人”本身被工具化时,发展也就失去了其最终的意义。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