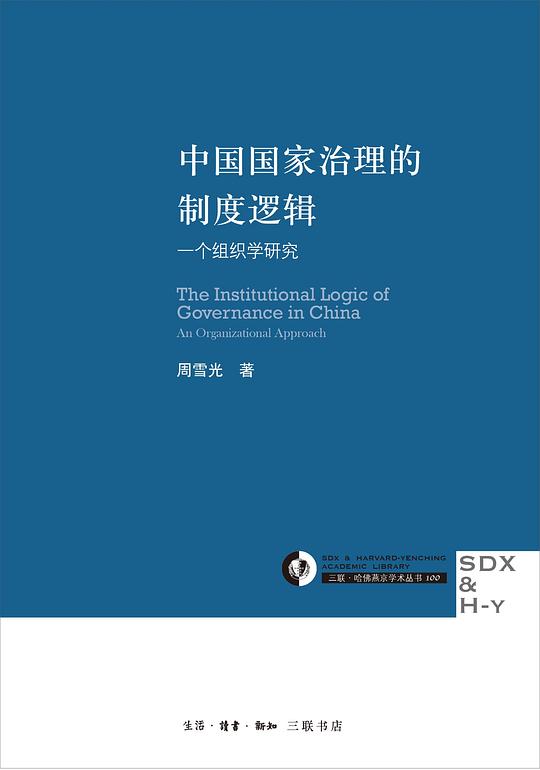
金秋: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书评(上)
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无疑是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内一座里程碑式的学术贡献。面对纷繁复杂、时常看似矛盾重重的中国治理现实,众多研究或流于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批判,或陷入具体政策得失的琐碎臧否。周雪光的这本著作则另辟蹊径,它并未耽溺于对威权体制下光怪陆离之现象的简单道德评判,而是严格遵循其在序言中所立下的学术圭臬——“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作者以组织社会学冷静而锋利的“手术刀”,对当代中国国家机器的内部构造与运作肌理,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湛细致的体制解剖学研究,其理论深度与经验洞察力,为我们理解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治理体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智识资源。
本书的核心论点,围绕着一个被作者精准识别并反复论证的深刻矛盾展开,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周雪光指出,中国政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旨在维系国家最高决定权的统一与权威,然而这一体制在面对广土众民、情势多样的治理现实时,又必然削弱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治理”能力。全书的精髓,在于系统地揭示了整个国家机器为应对并维系这一根本矛盾,而在漫长的历史与当代实践中演化出的一整套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无论是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还是“政治教化的礼仪化”与“运动型治理”的周期性介入,抑或是基层政府间普遍存在的“共谋”与“谈判”,这些看似“失范”或“非理性”的组织行为,在周雪光的分析框架下,都被清晰地解读为维系这一矛盾体得以持续运转的、具有内在功能理性的适应性机制。作者的分析,使得那些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政策执行偏差、制度规避乃至组织失败,都获得了逻辑上的自洽性。
周雪光的分析框架,因其严谨的学科自律与深刻的经验洞察,其解释力毋庸置疑。然而,恰恰是这种严格遵循组织社会学“价值中立”与功能主义的解释路径,使得本书在揭示了体制“如何运作”(How)这一功能性问题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悬置、甚至“中立化”了更为根本的政治学追问:这一治理逻辑背后的权力属性、统治目的及其规范性意涵究竟为何?当一种组织行为被证明为对系统维系“有效”时,我们是否也应同时追问,这个“系统”本身的正当性与道德基础何在?因此,本篇书评的旨趣,并非意在挑战周雪光卓越的实证观察与逻辑推演,而是在其坚实的分析基础之上,重新注入一个政治学的维度,试图将组织行为的“功能逻辑”还原为威权主义的“政治逻辑”。换言之,周雪光为我们精湛地绘制了一幅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与运行图谱,而本文则旨在追问这部机器为谁服务,其最终驶向何方。
为此,本文将在充分吸收周雪光理论创见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批判性对话:首先,我们将审视本书的韦伯理论根基,即“君主官僚制”这一核心概念,并尝试引入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视角作为必要的理论补充,以揭示当代中国“一统体制”的现代极权特质。其次,我们将重新解读作者独创的“控制权”理论,论证其在管理主义话语之下,实为一套贯彻政治控制与干部规训的精密艺术。再次,本文将对周雪光所识别的各项“适应性机制”进行规范性重估,将其从功能性的“权宜之计”重新定义为威权体制无法根除的系统性“病理”,这些病理以牺牲法治与公共理性为代价来换取体制的苟延。最后,我们将探讨本书国家中心视角下“社会”的缺席,反思这一整套强大的“治理逻辑”对于一个自主公民社会的形成所构成的根本性制约。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希望能够深化而非否定周雪光的贡献,将一部关于“治理的制度逻辑”的杰作,进一步引向对“统治的政治逻辑”的深刻反思。
一:韦伯的遗产与列宁的幽灵——“君主官僚制”之外的政党国家属性
周雪光的分析,始于一个极具理论雄心的起点:他试图为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治理现象,寻找一个贯穿历史与当下的、具有高度解释力的一致性分析框架。为此,他在本书第二章“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中,创造性地回归并激活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遗产,特别是其关于支配形式(forms of domination)的经典类型学。周雪光精准地指出,欲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内在机制,必先辨识其在国家支配形式中的结构位置,而这一位置,与韦伯笔下基于法理型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的现代官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周雪光的核心诊断是,从中华帝国到当代中国,其国家支配形式在根本上更接近于韦伯所定义的“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他将其进一步提炼为更具历史情境感的“君主官僚制”。这一概念的启发力量在于,它一举抓住了中国治理结构中一个至为关键的特征:在看似等级森严、规则细密的官僚科层体系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凌驾于所有规则程序的最高权威——即君主(皇帝)的“专断权力”(arbitrary power)。在这种支配形式中,官僚体制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其自身所代表的非人格化法律规则,而是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授权与委托。由此,整个官僚体系与君主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人身依附与“向上负责”的关系。官员的录用、升黜乃至生杀予夺大权,最终都掌握在君主之手,这使得官僚的行为逻辑必然以揣摩上意、完成指令为首要考量,而非严格恪守程序正义。周雪光的论述清晰地揭示,正是这种“君主官僚制”的底色,造成了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彼此排斥的恒久张力——皇权需要官僚体制作为治理工具,却又时刻提防其因体量庞大和信息垄断而产生的组织惰性与利益固化;官僚则在人身依附的框架内,发展出种种非正式的规则与网络来规避风险、谋求生存。这一深刻的洞察,为本书后续章节分析当代治理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行为的背离等现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石。可以说,周雪光借用韦伯的视角,成功地为理解中国国家机器为何“形似”现代科层、而“神似”传统王朝运作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解释起点。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精辟的起点上,韦伯遗产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将当代中国国家简单地类比为“君主官僚制”的现代延续,尽管在捕捉其历史惯性与人治色彩方面极具启发性,却也在无形中遮蔽了当代中国政体一个更为根本的、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属性。韦伯的理论工具箱,在面对一个以列宁主义为组织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现代政党国家(Leninist Party-State)时,显得力不从心。“君主官僚制”的分析,精于权力运作的形式——一个拥有专断权力的主权者与一个对他负责的官僚体系——却相对淡化了那个主权者本身的性质、其权力的来源,以及驱动整个体系运转的意识形态内核。当代中国的“一统体制”,其真正的“君主”,并非仅仅是某个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是作为历史进程先锋队的、组织化的政党本身。这是一个超越了传统皇权的、我们或可称之为“组织化皇权”的现代构造。
因此,当我们审视周雪光在第一章导论中提出的维系“一统体制”的两大核心机制——“官僚制度”与“观念制度”时,就必须引入列宁主义的视角来对其进行政治性的再解读。周雪光将“观念制度”视为维系认同与顺从的机制,并将其与历史上儒教文化的功能相提并论。这一观察无疑是敏锐的,但他或许低估了两者间的本质差异。当代中国的“观念制度”,其核心并非一套旨在维系社会伦理与和谐的文化传统,而是一套具有明确政治目标、旨在进行社会动员与改造的、排他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所要求的并非文化上的认同,而是政治上的绝对忠诚。同样,其“官僚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与管理机制,其首要标准也并非传统科举所标榜的才学或德行,而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可靠性与执行力。换言之,在韦伯的“君主”背后,潜藏着一个列宁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以其严密的组织、全能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重塑了“一统体制”的内涵。这个体制的控制深度与广度,是任何古代帝王所无法想象,也无法企及的。
要真正把握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我们必须将周雪光的组织学分析,置于一个更具政治学穿透力的理论框架之下,即“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理论。无论是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勾勒的极权主义模型,还是弗朗茨·舒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中对“党 - 政二元结构”的经典分析,抑或是魏昂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对单位体制下庇护 - 依附关系的精辟论述,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权力核心与组织中枢。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确保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指令统一性,这正是“一统体制”在当代的制度化身,其效率与刚性远非古代王朝的君臣关系可比。党的干部管理制度(Nomenklatura System),则将全国范围内的关键职位都置于中央组织部门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这构成了一个比任何皇权任命体系都更为系统、更为严密的“向上负责”的激励与惩戒网络。
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周雪光全书所聚焦的核心矛盾——“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时,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便豁然开朗。这与其说是一个普遍性的组织管理困境,不如说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根本性政治两难。一方面,作为维系自身存续的根本前提,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一统江山”的绝对领导权,确保政治安全,这便是“一统体制”的政治实质。任何可能导致权力失控、威胁中央权威的“有效治理”形式——例如真正的地方自治、独立的司法审查、自发的社会组织——都在被严密防范之列。另一方面,在革命意识形态褪色之后,政权的合法性日益依赖于其提供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治理绩效,这便是对“有效治理”的现实需求。
于是,周雪光笔下那个在集权与放权之间摇摆、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之间游走、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切换的庞大官僚体系,其一切行为选择的元逻辑,便是在“确保政权安全”这一最高政治目标约束下的“追求执政绩效”的次级目标。组织的“有效性”必须绝对服务于政权的“安全性”,一旦前者可能对后者构成任何潜在威胁,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加以限制、扭曲甚至牺牲。这一根本性的政治排序,是理解所有周雪光精湛分析的“制度逻辑”背后,那些看似矛盾的决策偏好与行为选择的最终密码。周雪光的韦伯式框架,为我们揭示了这部巨大机器的精密齿轮与传动机制,但只有引入列宁主义政党的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驱动这部机器运转的“第一推动力”及其无法摆脱的政治宿命。可以说,周雪光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木偶戏,但他将提线的手指指向了一位韦伯式的“君主”;而我们认为,那些看不见的提线,最终汇集于一个更为强大而隐秘的、名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幽灵之手。不识此幽灵,则对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理解,终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二:“控制权”的分配抑或政治控制的艺术?
如果说周雪光对“君主官僚制”的历史溯源为我们理解中国治理的宏观背景提供了深邃的洞察,那么他在本书第三章“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中独创性地提出的“控制权”(Control Rights)理论,则为我们深入国家机器的内部肌理,提供了一套极为精巧的分析工具。作者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不完全契约和产权的理论,巧妙地将政府内部模糊而笼统的“权力”概念,分解为三个可供分析和观察的具体维度: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这一理论创造的卓越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一个政治学的核心议题,转化为一个组织学上可操作、可测量的分析框架。
在周雪光的界定中,“目标设定权”是科层权威关系的核心,体现了上级为下级设定任务的权力;“检查验收权”则附属于前者,是上级核查任务完成情况的权力;而“激励分配权”——即对下属进行奖惩、考核的权力——则具有可分离性,可以保留在上级手中,也可以下放给中层管理者。通过观察这三种控制权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委托方 - 管理方 - 代理方)的不同分配与组合,周雪光清晰地勾勒出几种迥异的治理模式:从中央牢牢掌控所有控制权的“高度关联型”(运动式治理的组织形态),到中央设定目标、保留检查权,但将激励权下放给地方的“行政发包制”(常态治理模式),再到中央仅保留象征性权威的“松散关联型”。这一分析框架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的精度。我们不再满足于“集权”或“分权”这类笼统的标签,而是能够具体而微地辨识,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和历史时期,究竟是何种权力被下放,何种权力被保留,以及这种精细的权力配置如何塑造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无论是“层层加码”还是“合谋共谋”。可以说,“控制权”理论是周雪光对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权力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进行动态流转的精密地图。
然而,也正是这一框架的精巧与“技术中立”,使其带有强烈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色彩,从而在不经意间,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控制问题,转译成了一个近乎企业内部的委托 - 代理难题。在周雪光的论述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模型化为公司总部与分部、委托方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挑战在于信息不对称与激励不相容。这无疑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但从政治学的批判视角审视,这一框架的分析性中立,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些“控制权”在中国威权政体中的首要功能与根本属性:它们首先并非追求组织效率的管理工具,而是贯彻党的意志、确保政治忠诚、实施全面社会控制的政治艺术。其运作的逻辑起点,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最大化”,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控制最大化”。因此,我们的任务,便是对这套“控制权”理论进行一次政治学的解构与再解读,揭示其管理主义话言之下的权力本质。
首先,让我们审视“目标设定权”。在周雪光的管理学框架下,这似乎是一个相对中性的任务指派过程。然而,在中国政治的现实语境中,“目标”本身即是高度政治化的。自上而下设定的各项指标——无论是大跃进时期的“以钢为纲”,还是之后的 GDP 增长率、计生指标,乃至当下的“维稳”任务——其本质并非科学的绩效管理目标,而是执政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维护政权安全而确立的核心政治任务。因此,“目标设定权”的行使过程,与其说是任务分配,不如说是将党的政治意志层层分解、量化,并通过行政科层体系向下传递压力的过程。这正是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压力型体制”的源头。在这种体制下,目标的设定并非基于地方的实际情况与可行性,而是基于中央的政治决心。下级政府并非平等的契约方,而是必须无条件接受并完成指令的政治下属。因此,周雪光观察到的“层层加码”现象,其根源不仅在于信息不对称下的自我保护,更在于政治高压下输诚与“政绩竞赛”的必然结果。
其次,“检查验收权”的政治意涵同样远超其管理功能。周雪光将其视为确保“契约”完成的品控环节,这无疑是其功能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检查验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权力的展演与政治纪律的审查。那些由上级派出的检查组,其角色远不止于“验收员”,他们是中央权威的流动代表,是政治上的“钦差”。周雪光在书中敏锐地观察到检查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与戏剧性,例如“突然袭击”式的检查方式。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为了获取“真实信息”,更是为了制造一种政治威慑,时刻提醒地方官员,中央的目光无处不在,任何偏离轨道的行为都可能受到惩罚。检查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与“共谋”,与其说是信息博弈,不如说是地方官员在绝对权威面前,通过非正式渠道寻求政治庇护与风险规避的生存策略。因此,“检查验收权”的真正威力,不在于其发现问题的技术能力,而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能够随时启动政治惩戒程序的专断权力。它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巡视功能异曲同工,旨在确保整个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绝对忠诚与步调一致。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对“激励分配权”的政治学还原。周雪光的框架将此视为对下级行为进行奖惩的权力,这在形式上完全正确。然而,这一权力的真正内核,正是列宁主义政党国家赖以维系统治的基石——干部管理制度。在中国,对官员的最大“激励”是政治生命的延续与职业生涯的晋升,最大的“惩罚”则是纪律处分、撤职乃至政治清洗。而决定这一切的,并非一个中立的绩效评估委员会,而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所掌控的一整套干部选拔、考核、任免与调动体系。周黎安广为人知的“晋升锦标赛”模型,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官员为谋求晋升而展开激烈竞争的动态,周雪光的分析也与之呼应。但这幅图景需要补充一个关键性的前提:这场“锦标赛”的最终裁判,即党组织,其评判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才是业务性的。一个官员的晋升,不仅取决于其治下的经济数据,更取决于其政治忠诚度、路线觉悟、与上级领导的个人关系,以及在关键政治时刻的“站队”表现。因此,“激励分配权”的分配与行使,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塑造和规训整个官僚队伍,使其成为驯服工具的核心机制。当周雪光论及“激励分配权”的下放或集中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党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地方干部控制的松紧程度的调整。
综上所述,当我们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重新置于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政治框架下进行审视时,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便浮现出来。所谓的“控制权分配”,其本质并非一个组织内部为解决管理效率问题而进行的功能性授权,而是威权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控制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精密安排与统治艺术。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一个基于契约和信息不对称的“委托 - 代理”关系,而是一个基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等级森严的“统治 - 服从”关系。地方政府面对中央,其根本困境并非“代理人风险”,而是政治不忠诚所带来的生存风险。中央政府的核心关切,亦非单纯的“代理成本”,而是如何确保其政治指令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防止任何形式的政治偏离。周雪光以其组织社会学家的冷静与精细,为我们描绘了这套控制体系的技术性运作细节,其贡献不可磨灭。然而,作为政治学的分析者,我们必须穿透这层技术性的管理主义话语,直面其背后那个更为坚硬的政治内核。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套看似“逻辑自洽”的制度安排,其最终服务的,并非抽象的“国家治理”,而是具体的、中共作为执政党的长久统治。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