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纵:“冤”与“青天”之间与之外:中国抗争政治的一个侧面
2006 年出版的欧博文(O'brien, Kevin J.)与李连江合著的《中国农村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一书,是研究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绕不过去的一本文献,两位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rightful resistance”一词(学界往往通译成“依法抗争”)也在各种当代中国研究中被频频引用。在众多引用当中,自然不全是对这一概念的正向评价,也出现了一些“逆流”,例如赵鼎新就认为二位教授的“依法抗争”是一个失败的概念,缺乏原创性,只是跟了斯科特(James C. Scott)“日常形式的抵抗”的风。笔者会在后文中对这一争论做出个人的评价与解读,并试图借对“依法抗争”的重考切入当代中国的一些重要议题。不同于赵鼎新对“依法抗争”的轻蔑,本文认为欧博文与李连江基于大量田野调查提出的这一概念是很立得住脚的,虽然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对中国”公民权“的成长做了一些期望,现在回头去看自然觉得“不切实际”,但作者的态度与分析仍是很泠静的,也为回答“中国的为什么未能发展出公民权”这一命题提供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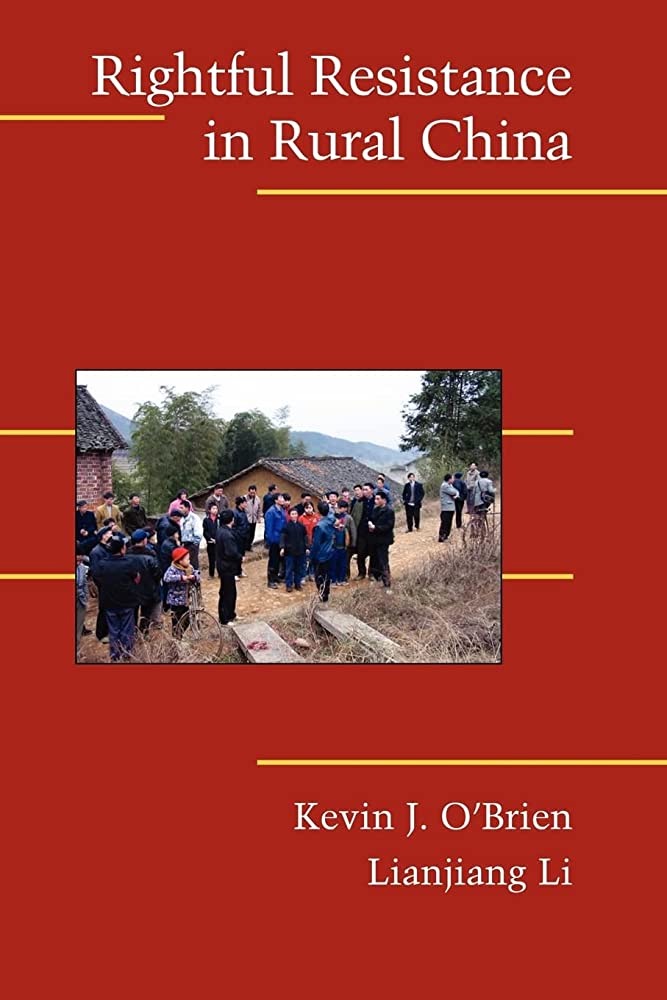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基于丰富的田野调查,探究了自 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农民抗争现象,这时的农民抗争往往与基层政府征收过量的税费有关。在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激起了农民的广泛抗争。虽然同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不少缩减农民负担的政策与条例,但基层政府并未执行这些政策,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偏差”,为农民的抗争提供了切入口,而地方并未照章执行的中央文件或相关法规,则为农民的抗争行为提供了正当性,农民往往试图通过援引“中央精神”来给基层官员加压,从而约束他们的行为,农民同时也试图在更具权势的政府层级中寻找到支持农民诉求的官员,获得他们的“批示”或“指示”,并借此增加自己抗争行动的正当性,或者直接让这些偏向农民的高层官员直接向基层干部施压。在农民的眼中,中央的“好政策”往往被地方的基层官员扭曲或忽略,因此中央需要他们的帮助去获得有关基层官员不忠诚与行为不当的信息(P45-46),通过表达自身抗争行为对中央的“意义”,农民在内心中完善了自身行为的逻辑,农民的抗争行为不仅仅基于“中央的政策没在地方好好实施,因此我们要用中央政策来给地方官员施压”,更是基于“自身的抗争行为对中央的统治有利”这一“思考”之上,也就是表现了自身行为对中央的“有用性”。但同时,这些试图在体制内解决问题的“依法抗争”并不经常能得到农民们预期的效果,这就激发了农民们更加激进的行为,直接组织集体行动与基层干部进行对抗。尽管如此,这些直接对抗基层干部的农民依然对“中央”保持了相当高的政治信任(P90)。
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也对农民上访过程中类似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借此描述了一套“官民共享”的思考逻辑,在基层干部眼中有这样一輻农民的图景,“即‘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少数易受数弱的群众+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当他们与农民打交道碰到阻力时总会将具体的人分别与这幅图景的某个位置相对应,从而再来考虑相应的化解之道一—依靠,教育或打击。我们可以将这种对应方法称之为‘人民一坏人’对号法。”与“人民群众—坏人”这类“革命化”区分法并存的是“刁民—顺民”区分法,这一区分法也会被基层干部在描述上访农民时使用。同时,农民心中也有一幅对于中国官僚的“差异化”图景,“‘闪着神奇光辉的中央 +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当农民与政府打交道时常常会将某个官员与这幅图景中的某个位置相对应,我们可以称之为‘清官一贪官’对号法。”农民与官员的“认知图景”似乎延续了帝制时代的某种“传统”,“皇帝好,贪官奸臣坏,国家出问题就是皇帝被贪官奸臣蒙蔽,大部分老百姓都善良质朴,只有一小撮刁民才会起来闹事,甚至是良心坏到去造反”。但实际上,在当代党国的话语体系下,“传统”的含义不断变迁与重塑,甚至农民与官员的这种相当“传统”的“认知图景”,也可以说是后四九年党国政治的“新发明”,或者说是党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从官员的认知图景来说,“刁民——顺民”的区分法和后四九年党国“革命的”身分政治划分保持了高程度的耦合,“革命”的“人民”就是“顺民”,“反革命”的“坏分子”则是典型的“刁民”,在这种“革命——反革命”/“人民——坏分子”/“根正苗红——黑五类”之类二分法划分之下,配合上后四九年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与路线和权力斗争,及其随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身份的划分,“顺民——刁民”的二分法就在后四九年的党国政治实践中得到再现。而基层农民对中国官僚的认知图景,虽然在表面上和“传统”的“明君——奸臣”/“青天——奸臣”等分类法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看起来是某种帝制“传统”的延续,但实际上这种“传统”仍和后四九的党国政治实践高度相关,不可分割。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后党国政治”和“帝制传统”是断裂的两种不同政治类型,而是试图说明后四九的政治实践与运行虽然表面上“高度的反传统”,但实质上在种种政治运动与各层级权力斗争之中,其以高度反传统的话语重新实践了帝制的专制主义传统。例如欧博文与李连江就在书中指出:“这种信任模式(引者注:指好中央——坏地方的认知图景与政治信任模式)肯定是由现政权培养起来的。自 1949 年以来,官方媒体几乎不间断地开展宣传活动,将大部分成就归功于中央,并将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地方官员或民众中的‘坏分子’。”(P46 注 18)并且在 1949 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与高层的权力斗争中,“明君被奸臣蒙蔽”的叙述也被反复地灌输给民众,例如在不断产生的 xxx 反革命集团中,毛泽东“红太阳”的明君圣主形象被反复地确立,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为了保持党国话语体系的连续性,在决议后四九年历史的官方叙事之时,当局再次使用了这一逻辑,将“毛被四人帮和林彪所欺骗”确立为官方的唯一叙事灌输给大众。
在这样的认知图景之下,农民借用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不一致来为自己的抗议行动寻求合法性,实际上完成了“误识”或“官方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农民的抗争行为成为官方施展权力的一个支点。如果农民的依法抗争成功,农民成功借中央文件或上层官员的权力约束了地方官员的不轨行为,这自然增强了农民心中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好——地方坏”这样的认知图景,但是农民依法抗争失败,无法通过中央的好政策约束地方的坏行为,这种失败则直接强化了农民的“中央好—地方坏”的认知图景,依法抗争失败就是因为地方的坏分子势力太大,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央的合法性。试图从这样的抗争行为中寻找“公民权”的兴起,也许注定会是失败的。虽然作者们指出农民在维权时开始使用“公民”、“公民权”或“权利”这样的词语,但是这些权利性话语往往和“坚持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搞成了“中体西用”,例如“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有义务为贫困的农民和党站出来”(P118 注 3),这时维持“中央的好形象”不仅仅是农民的一种“抗争策略”,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合被农民所接受,并在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抗争策略时,这种“意识形态霸权”被反复地加诸农民之上,使之难以逃离。

接下来转向对赵鼎新与李连江二人论战的讨论。在赵鼎新的评论中,他并未提出他对“依法抗争”这一概念的理解,而是用他先用自己提出的一套“方法论”来抽象的谈论为什么“依法抗争”这个概念不好,唯一一个算是对“依法抗争”这一概念的具体评论则是在指出,“依法抗争者掌握着较大的能动性”,他们并不会把抗争手段局限于“依法抗争”。他立马又举了几个他“听说”的案例,并指出这些案例没有“法律和政策支持”,都不是“依法抗争”,“这类抗争之所以获得成功,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怕事情闹大,结果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一普遍现象”。或者根据他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的第二版序里所言,“中国集体抗争事件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从上访、请愿、绝食、怠工、罢工、示威游行、骚乱、扣留甚至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暴力对抗,应有尽有,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谓的‘依法抗争’或‘以理抗争’。”由此观之,可见赵鼎新并未理解欧博文与李连江所提出的“依法抗争”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他的理解中,似乎仅仅把“依法抗争”从字面上理解为“民众仅依靠法律或中央政策进行抗争”,却忽略了欧博文与李连江在书中作的各种动态与延伸分析。就像是农民在采用对抗基层官员的依法抗争之时,手段并不会局限于“法律过国家政策”,“诉诸舆论和大众情感”也是其手段之一,二位作者在其著作中指出,“在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的受众正在扩大,不仅仅只面对那些对农民抗议持好感的上级官员。依法抗争的反抗者现在经常求助于另一个第三方——公众。”(P92;P85-88)“依法抗争”中的“法”字,含义是很宽广的,党中央仅在字面上支持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符号,甚至某一上级官员的“批语”或“批示”(P83),都可以成为“依法”(rightful)的来源。
在赵鼎新的“方法论”构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并不倾向于将“抗争者”视为“受害者”,或者说他并不想将抗争者赋予“道德优越性”。在赵的理论构建中,抗争者不仅不是“弱势群体”,反而是受了国家恩惠还“不领情”的“白眼狼”,用赵教授的原话来说就是“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读过赵教授《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序的读者,恐怕不难看出赵教授论述中那种“国家做了好事一堆,但是老百姓居然还不领情,依然起来抗议”的语气。笔者仅在此处截取一小段:“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持社会稳定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当前中国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仍然大都是贪官污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大大开放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集体抗争事件的报道,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集体抗争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的宗教政策这几年在不断走向宽松,但不少家庭教会的领导者并不领情,而政府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对策。中国政府近年为了提高少数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资金不在少数,但少数族群闹事却有增无减。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在其体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为维持社会稳定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但集体抗争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除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将目前发生的集体抗争事件纳入体制的轨道。”在赵的这种论述中,民众的抗议往往与“体制问题”无关,更像是对“利益分赃不均”的气愤,只要民众的经济利益得到了满足,自然就不会有“社会运动”或“抗争政治”,却忽略了这个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体制,在制造经济绩效的同时,同时也是各种抗争政治与公众不满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笔者再暗自揣摩一下为什么赵教授对“依法抗争”这个概念这么火大,很可能是欧博文与李连江二位教授的“依法抗争”概念戳中了赵教授“绩效合法性”这一概念构造的“暗门”。在赵的“绩效合法性”概念中,支撑党国合法的支柱就是“经济绩效”,如果党国经济下滑,它就会丧失它的合法性,似乎欲求不满的白眼狼老百姓们就会起来闹事。而欧博文与李连江却通过“依法抗争”这个概念讲述了另一个现象,哪怕农民利益受损却依然对“中央”保持了高度的认同,表现出一幅“忠诚的反对者”的面相。
在赵鼎新的理论体系中,“国家——社会”关系是其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在他的论述中,“国家”与“社会”往往作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而存在,因此抗争政治往往意味着“社会”反对“国家”,或者用赵的原话来说,“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将目前发生的集体抗争事件纳入体制的轨道”。但是如果我们透过”依法抗争“这个概念来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或者说“党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情况,在“依法抗争”中,农民游走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灰色地带,采用支持国家的一部分去反对国家的另一部分的策略,跨越国家与社会间的边界,或者说,模糊了国家与社会间的边界,使之不那么分明。如果审视“中国社会”的起源,可以发现,改革之前中国并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和党国体系异质的体系,党国体制通过城市中的单位体制与农村中的公社体制将其权力延伸到最基层,并且借此完成计划经济的实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待遇差别”,但是并不能说这是一个城乡二元的体制,因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支配经济运作的根本力量仍是同质的国家权力与政治计划。因此,“社会的生产”是一个改革后出现的新现象。借着公社体制的解体与城市中单位体制的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出现,后毛时代才出现了“社会”这个与国家异质的力量存在。

但是,中国的“社会”往往并不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的景观,同时,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也和中国“社会”的独特起源有关。就像是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与龚小夏在研究六四运动时就发现工人与学生两股社会力量在心态上存在的分歧,工人们把学生视为精英,而学生们似乎也这样认为自己,但是这种工人与学生联合的失败,真的可以只由学生的“精英主义”来解释吗?可能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起源”与“社会的碎片化”角度来回答“学生为什么会有精英主义”,总不能归因于“因为学生的特点是精英主义,所以学生有精英主义”这样的糊涂答案。“身份等级制”或者说“身份区隔”是毛时代的一个典型特点,“学生”与“工人”之间存在巨大的身份差距无法联合,并不只是改革后才有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毛时代的遗产”。而中国后毛时代的“社会”,就是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毛时代党国中诞生,配上至今仍未拆除的户籍制度与至今仍未消弭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当局对“结社”的严厉打击,社会的碎片化似乎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不仅是“横向的碎片化”,甚至也是“纵向的等级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国便可利用民众在“身份等级”中的追逐与攀爬,将之作为一种“统治术”,来降低民众的联合意愿。
“只会与国家作对”看起来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尤其在“国家安全”与“维稳”压倒“和谐社会”的习时代,而“民众抗议只因分赃不均”也不太能概括中国抗争政治的全部面相。“依法抗争”这个概念中实际上展现了一个更复杂的中国抗争政治图景,哪怕“民众真的试图通过抗争政治为自己盈利”,依然要表现出自己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就像在被赵教授暗喻为“来百姓因为分赃不均才起来抗议”的乌坎运动中,也多次出现“请求中央伸冤”这样的口号或是“拥护共产党”这样的标语。更何况,中国的民众抗争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分赃不均”,而是因为“合法权益受损”,赵教授把老百姓的抗争归于“老百姓白眼狼”,这怕是“国师之心天下皆知”了吧。但同时,认为“抗争政治”能带来“公民意识”的觉醒,恐怕依然是一厢情愿,君不见“白纸运动”后《流浪地球》与《满江红》等主旋律电影的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