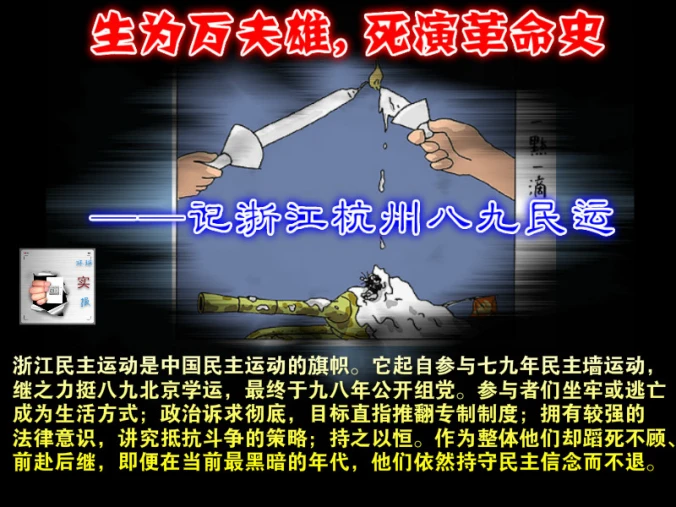
吴高兴: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1989 年“六四”惨案的枪声响后,在浙江的杭州和其他中小城市,甚至在一些乡村,都出现了民众的自发抗议行动。嗣后,浙江当局按照北京的指示,对各地的抗议人士实行了严厉的镇压。按浙江省当局当时的规定,“八九”民运期间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凡判决以后,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一律送到杭州市郊的临平镇省第四监狱集中关押。
从 1989 年 10 月开始,全省各地的政治犯和良心犯陆续送往四监(早在是年 8 月,仙居县液压件厂青年工人杨忠信就被送到乔司劳改农场,后来转送临平四监,他因书写和张贴抗议“六四”屠杀的标语,被台州中级法院判刑 5 年,首开浙江省迫害“六四”良心人士的先例),到 1990 年夏初,总数为 45 人(见附表),其中年龄最小的,是绍兴嵊县职业高中刚满 18 周岁的学生金秀元;年龄最大的,是 59 岁的玉环县楚门镇退休工人、联防队员叶良才。此外,1991 年春天,在北京判决、原籍富阳的王有才也被转送到四监关押,虽然不与我们一起,但离我们不远,跟我们偶尔有些接触,比如晚上看电影时,王有才就在我们旁边。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关押在四监的 45 名难友,远远不是全省“八九”民运政治犯和良心犯的总数,因为凡是被判劳教、拘役、管制,以及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都不在四监——例如,在临海,就有一个叫张国平的工人因在街头发表演讲抗议北京屠杀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还有人因在旅馆电视机上书写标语“打到邓、杨、李”而被判两年徒刑的,且据我们了解,个别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也没有送到四监。其次,据说四监还有其他非“八九”民运的政治犯,因不与我们一起,无法了解其具体情况。
开始,我们被编为入监队六组,以后由于人数增加,1990 年初夏改编为直属中队,归监狱当局直接管辖。在这些政治犯良心犯中,刑期最长的是原杭州花圃工人马德良(因组织“劳动党”被判 13 年),其次是原浙江教育学院学生毛国良(7 年),以及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伟平(9 年,1990 年底改判为 5 年)。到 1993 年 9 月中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毛国良被释放,狱中只剩下马德良一人尚在杂务队服刑,四监的其他“八九”民运政治犯已全部获释。
我们在四监的遭遇大体上可分为“入监队六组”和“直属中队”两个阶段。入监队六组时期,全国政治气候仍然非常紧张,监狱当局对我们以惩罚为主。他们专门派了三个刑事犯(其中两个穷凶极恶,一个是被判刑 16 年的盗窃犯,另一个是外地的流窜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性格比较平和、盗卖文物的犯人),昼夜 24 小时监视我们,并且担任我们的犯人组长和“护监犯”。为了防止我们串通一气,监狱当局禁止我们三人以上交谈,禁止与亲朋好友通信,禁止看同犯的判决书,并且不准我们看任何报纸(而刑事犯是可以看报纸的),明令我们必须绝对服从三个刑事犯的管理,声称他们“受队长(管教)的委托”。毛国良初来四监的当天,队长按惯例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要求,他如实表示了要看报纸的愿望,结果被关禁闭一周。1990 年 4 月,崔建昌和杨泽敏等几个学生凑在一起过生日,唱起了国际歌,结果有四人被关了 20 多天禁闭。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狱方经常召开批判会和讨论会,逼迫我们人人表态,批判所谓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他们在给我们训话时骂“方励之原来就是一个大右派”,“是美国的一条哈巴狗”,说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比卖国贼还不如”,甚至连“八九”民运前夕去世的艺术家赵丹也成为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骂赵丹“临死以前还要放个屁”(呼吁党不要再干预文艺创作了),还蔑称我们是“极少数人的政治牺牲品”,等等。除了精神折磨外,还对我们进行肉体上的惩罚,比如在寒风刺骨的腊月,强迫青壮年难友跳进齐腰深的水塘用脸盆挖泥;而到了骄阳似火的夏日,又强迫我们从事挑砖头上山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收工以后,还要我们在烈日底下进行队列操练,或者长时间丝纹不动地立正,多次折磨得一些身体虚弱的难友当场昏倒在地,美其名曰“行为养成”。这是直属中队成立以前的大略情况。
从 1990 年初夏开始,尤其是方励之出国避难以后,政治气氛并不像原来那么剑拔弩张了,狱方也对我们改变了策略,由原来的惩罚为主转为软硬兼施。他们将入监队六组改编为直属中队,指派了一个比较有政策水平的管教担任中队的“指导员”,换上了较为平和的刑事犯担任犯人组长和护监犯,这在客观上改善了我们的处境。1990 年底,李泽民仍然担任省委书记的浙江当局对“八九”民运政治犯实行大规模减刑,这种做法显然意在短期内全部释放“六四”受迫害人员,减轻历史包袱。为此,对长刑期的“六四”政治犯和良心犯进行改判,例如,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伟平因给美国之音打电话报道学生在省政府大楼降半旗为“六四”死难者致哀的消息,在北京特派员的督促下被重判了 9 年,1990 年底被改判为 5 年,不久即通过减刑予以释放。又如原浙江教育学院学生毛国良因在法庭上宣称自己犯了“爱国罪”,痛陈北京当局的屠城罪行,被重判了 7 年,1990 年底,上面派人到四监找毛国良谈话,要其表态认罪,答应给予改判,因毛国良拒绝认罪而搁置,不过仍然以减刑的形式,于 1993 年 9 月予以释放。
自从浙江省当局实行怀柔政策以后,特别是对“八九”民运政治犯和良心犯大规模减刑以后,狱方对我们的监管渐趋宽松和文明。中队指导员潘建民是个难得的作风正派、工作负责、处世严谨的开明人士,他多次向我们表示:“这里是监狱,我们凭判决书对你们实行监管,希望大家严格遵守这里的监规纪律,如果你们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尽量给予解决。”他一方面取消了入监队时期的批判会和讨论会之类的洗脑活动,另一方面又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劳动时间,遇到下雨天,往往就让我们在监舍里看书自学,有时晴天也这样。只要我们遵守监规纪律,就尽可能让我们在狱中的生活过得宽松一些,尽可能让我们多看点书,尽可能允许外面的亲友来看望我们。整个直属中队时期,虽然也曾发生过队长违规动手殴打甚至虐待难友的事件;青年难友中也免不了会有违反监规纪律并因此而受到惩罚;难友与队长之间也免不了会有脸红耳赤、言语冲撞的时候,但从总体上来说,以潘建民指导员为领导的中队队长们是对得住良心和历史的。不管是狱方实行恐怖高压政策,还是采取怀柔政策,以毛国良为代表的部分难友始终坚持抗争。1990 年 4 月 15 日,毛国良等部分难友秘密举行纪念胡耀邦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六四”惨案一周年期间,在毛国良带头下,绝大部分难友绝食两天以哀悼“六四”死难同胞。尤其使同监难友们终生难忘的,是集体抗议狱警殴打叶文相,迫使监狱当局公开道歉的一幕。1991 年 2 月 5 日,难友叶文相因不愿对队长点头哈腰而被狱警毛明拖到队部强迫罚跪,遭到拳打脚踢,这种违规违法的行径引起难友们的普遍义愤,在毛国良的带头下,大家当晚就自发举行绝食,给狱方造成了强大的压力。狱方召开直属中队全体犯人大会,以辩解、威吓和安抚相结合的策略,企图化解殴打叶文相之事所引起的不满情绪,遏止绝食。在大会上,吴高兴等一些难友挺身而出,有理有利有节地揭露和驳斥了狱方殴打叶文相的违法行径,宣称“我们要向省委、省政府,直至党中央、国务院控告你们的非法行为!”狱方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第二天,他们找犯人个别谈话,散布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一面以禁闭、隔离甚至加刑相威胁,一面又提前透露减刑名单,以此分化瓦解绝食队伍。在减刑和加刑的利诱威胁下,一些难友停止了绝食,在此关键时刻,毛国良在难友中宣告:“就是枪毙我们,也要绝食到底!”在众多难友的坚持下,最终迫使狱方公开承认错误。2 月 6 日这天晚上,狱方再次召开直属中队犯人大会,由中队指导员潘建民代表中队向我们公开道歉,表示“今后决不发生类似事件!”从而得到了我们的谅解,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做法当场博得了我们的一片掌声。
不过,怀柔政策也有它的负面效应。由于狱方竭力鼓励直属中队良心犯们“认罪”,检讨自己的“罪错”,通过“努力改造”获得减刑,这使得难友们的凝聚力大大减弱了。为了减刑,有的难友在年终思想汇报会上攻击别人“对共产党刻骨仇恨”,表示“要跟他们划清界线”,有的甚至以打小报告获取狱方的青睐。这样,随着狱中气氛的不断宽松,难友们的凝聚力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了,一些难友再也不愿意去纪念那个曾经令自己铭心刻骨的悲惨日子了,遇到狱中难免仍然会发生的个别难友受虐待的事,再也不肯施以援手而漠然无睹了。至 1991 年“六四”两周年期间,仍然以绝食哀悼国殇日的,就只剩下毛国良、陈龙德、吴高兴、王东海、叶文相、赵万敏、黄志道、付权、金秀元等 10 来个难友了!1991 年 8 月上旬的一天,原浙江师范大学学生黄志道早上出操穿拖鞋,被监管队队长叫出训话,由于挺身直视队长,拒不回答问话,被铐在监狱大门口的铁索栏上示众。毛国良见难友受辱,愤而冲出监舍警戒线,怒斥“这是法西斯行径”,结果与黄志道一起被关进禁闭室用电警棍长时间施以酷刑(毛国良出狱以后很久还留有伤痕)。当时虽有吴高兴、陈龙德、叶文相、付权、张金林、崔建昌等难友的据理抗争,但终因人心涣散,不能形成对狱方的强大压力,无法有效地实行救援。
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省对“六四”政治犯和良心犯进行集中关押,这客观上减轻了我们所受到的迫害和虐待,但是,仍然有两名难友在狱中精神失常:一个是丽水师专大一学生胡文奎,另一个是宁波市装潢工人邬伟海。
20 年来,人世沧桑,当年的难友们出狱以后,境况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有的走上了经商发财之路,如今腰缠万贯,跻身精英阶层,有的被安置到学校等国有单位工作,如今事业有成,自得小康之乐——这些人主要是当年的学生群体;第二部分是大多数,他们一直辛苦麻木地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就像当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忽然成为罪犯一样,如今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总不能走出贫困的阴影;最为清醒,从而也最为坎坷的是第三部分人,他们是一群不识时务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在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愿意放弃当年的理想,不愿意跟肮脏的现实同流合污,不愿意忘记 20 年前那惨烈的一幕,像精卫填海那样,执着地为重新评价“六四”和昭雪共和国的其他冤假错案、推动社会走向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艰难的人生征途中,免不了时时受到权势的打压,其中受迫害最深重的,莫过于陈龙德。1996 年“六四”7 周年期间,他因发起联名呼吁北京当局平反“六四”,被浙江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劳教 3 年,在狱中因不愿意认罪遭恶警残酷殴打,被逼跳窗自杀,跌断了股骨,又得不到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陈龙德今年 52 岁了,仍然拄着双拐孑然一身,靠父母的退休金维持生存。
最后,讲到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王有才,还不能不提董怀明和傅国涌。董怀明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原来是浙江嘉兴卫生学校的讲师,“八九”民运期间曾经担任北京工自联的特约评论员,被北京当局判了 4 年。他不是四监的难友,但 1993 年底到 1995 年之间与陈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等人有过多次接触,刘念春和张林就是由他介绍我们认识的,以后就失去了联系。推算起来,今年他应该有六十三四岁年纪了。傅国涌“八九”民运时才二十出头,擅自抛掉教师工作跑到北京去了,被处以 3 年劳动教养。他也不是四监的难友,但 90 年代中期和陈龙德、王东海一样也是浙江异议活动的带头人,因此 1996 年再次被处以 3 年劳教,现在成了国内著名作家。
此文初稿于 1993 年 12 月 16 日,当时因许良英先生想了解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的情况,由吴高兴执笔,经陈龙德、王东海、叶文相补充后定稿,并由王东海赴京面交许先生一份。作者后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反复修改,并于 2009 年 3 月 4 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