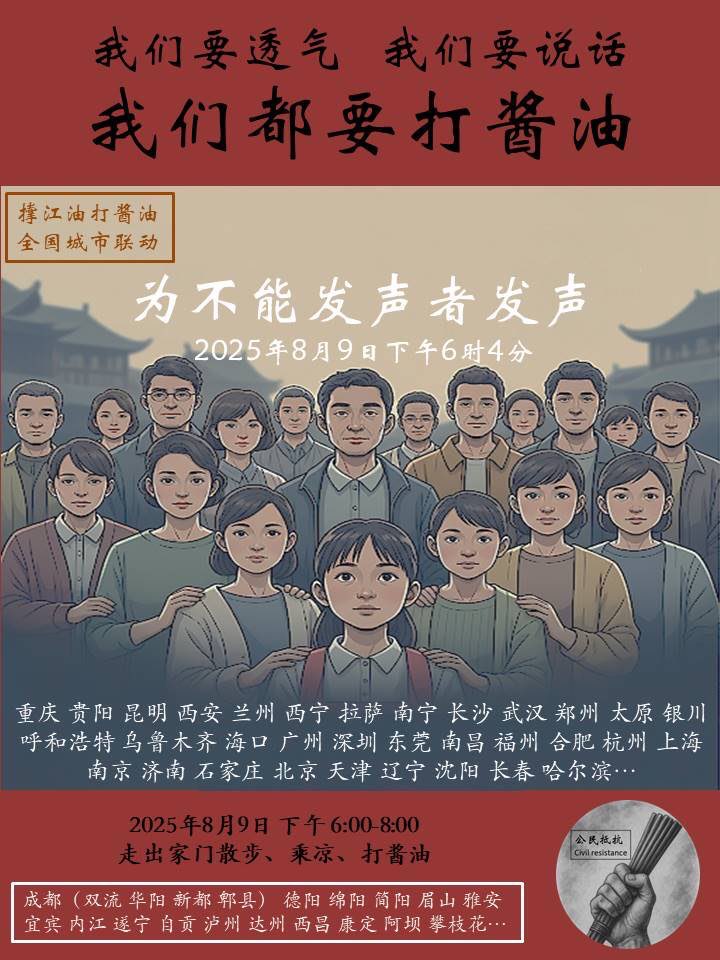
姜福祯:力量就是团结
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民间抗争,起点往往不是推翻一个政权,也不是为了争夺选票权力,而是从一件具体的、切身的利益与权利问题开始。人们面对的,也许是一条不合理的社区规定、一项无理的行政命令,或者一桩直接影响生计的苛刻措施。这些事件看似琐碎,却能瞬间触动集体的神经,因为它们关乎生活的尊严与基本的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的抗争大多是一种“抗命不服从”的和理非过程。它不是暴力冲突的同义词,而是社会成员用最直接的行动告诉权力方:这条规则不公,这项措施伤害了人。这种抗争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喊口号的音量有多大,而在于有多少人能够并肩站出来。
团结,是这种力量的本质。
一个人可以愤怒,但很容易被忽视;一群人可以抱怨,但如果各自为战,很快被分化瓦解。唯有当分散的声音汇聚成稳定的合唱,形成有序、持久的存在,才会迫使制定规则的人正视问题。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团结让强权顾忌,让不公退让。
团结并不意味着盲目跟随,而是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判断形成的自愿协作。在一次社区事件中,如果物业、公司、或政府部门出台一项明显加重民众负担的规定,个体的抗议很可能被敷衍或忽略。但如果几十、上百、上千人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持续聚集、表达、谈判,对方不得不权衡其代价与后果——这是团结的杠杆效应。
和理非,并不是软弱的代名词。它的“和”,是拒绝无谓的流血牺牲;它的“理”,是坚持逻辑与道义的底线;它的“非”,是“不合作、不配合、不承认不公规则”的拒绝。真正的和理非,是一种社会智慧:既不给对方使用暴力的借口,又不断积累压力,迫使不合理的制度调整。
这样的抗争,并不需要复杂的组织架构,也不必依赖宏大的政治口号。它的燃料是共同的处境,纽带是相互的信任。一个骑手的遭遇,可能成为两百个骑手的共同战斗;一户居民的困境,也可能引发整个小区的声援。团结往往从局部问题出发,却能激发出超越个人的公共意识。
然而,团结的最大敌人,不总是强权本身,而是冷漠与分化。有人会劝说:“算了吧,不值得冒风险”;有人会算计:“反正这事跟我关系不大”;还有人害怕卷入,于是选择沉默。这些态度会逐渐消解抗争的力量,让坚持者孤立无援。任何一次民间抗争,若失去广泛的支持,就很难在谈判桌上保住成果。
团结的另一个要素,是信息的透明与诉求的明确。模糊不清的目标会让参与者失去耐心,也给对方制造混乱的空间。反之,明确的、具体的诉求——比如“撤销某项规定”“降低某项收费”“恢复某种通行权”——不仅能让行动更聚焦,也便于衡量成败与调整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抗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别事件。它们像一条条细小的水流,汇入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盼之河。当一个群体成功维护了自身的合理权益,往往也为其他群体树立了信心和方法。今天是骑手的胜利,明天可能是教师、医生、工人或居民的胜利。团结的经验会在不同领域之间传递,形成社会自我修复的潜在机制。
当然,团结也需要自律与节制。抗争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伤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参与者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同时保留道义上的优势。赢得一场权益之争,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的正当性——这是让更广泛公众愿意加入、支持的关键。
最终,团结的力量不仅仅改变一条规则,更可能改变人们面对不公时的心态。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会让参与者意识到:我们并非孤立无援;当我们彼此支持时,就有能力撼动看似不可动摇的东西。这种信心,是抗争的最大收获,也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
力量就是团结——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次真实行动的总结。它告诉我们,即使在资源有限、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团结依然是弱者最坚实的盾牌与最有力的武器。它让人们明白,权利不是被施舍的,而是靠集体的坚持与智慧赢得的。
当利益与权利遭遇不公,当制度与规则失去合理性,民众的抗命与不服从,就是一堂堂生动的社会课。团结,让这堂课有了足够的分量,让答案不只是愤怒,更是改变。
2025 年 8 月 12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