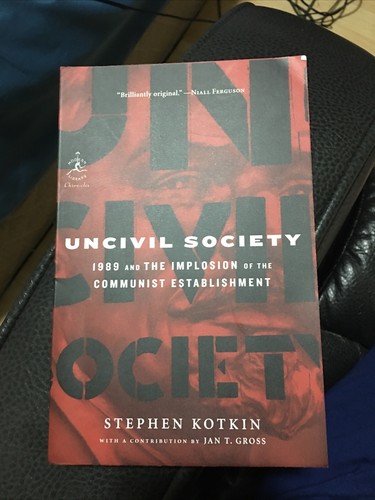
张东云: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书评(上)
1989 年,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为“奇迹年”的时刻,以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为高潮,宣告了冷战格局的终结,也似乎为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画下了一个明确的句点。对此后三十余年的学术界而言,如何解释“苏东剧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两种宏大叙事主导着公众乃至学界的想象:其一,是一种带有浓厚目的论色彩的英雄叙事,将 1989 年的崩溃归因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觉醒与抗争,认为是异议分子、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道德勇气最终战胜了僵化的极权体制;其二,则是一种“革命失窃论”的悲观论调,认为旧体制的权贵精英(nomenklatura)在关键时刻摇身一变,窃取了转型果实,将一场本应属于人民的革命,异化为一场资产的重新分配。
正是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叙事之间,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的《非公民社会:1989 与共产主义体制的内爆》(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一书,以其深刻的洞察与犀利的笔锋,提供了一个极具颠覆性与说服力的全新解释框架。柯特金的核心论点明确而尖锐:1989 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连锁式崩溃,其根本原因并非来自外部“公民社会”的胜利,而是共产主义建制派本身——一个他独创性地称之为“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的统治精英群体——从内部发生的“内爆”(implosion)。此书的重大贡献,在于果断地将研究的聚光灯从长期被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反对派身上,转向了体制内部那庞大、复杂且充满内在矛盾的统治机器。
一、
1、对“公民社会”乌托邦的祛魅
长期以来,解释 1989 年苏东剧变的流行范式,往往简化为一场“公民社会”反抗极权国家的道德剧。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东欧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自发的民间组织,被塑造成一个统一且强大的行动主体,他们代表着良知与勇气,最终冲垮了僵化腐朽的党国体制。柯特金在本书的序言中便开宗明明义地指出,这种对“反对派”的过度关注,并将其“幻想为一个‘公民社会’”(fantasize as a“civil society”),无异于一场“漫长而毫无结果的探寻”(Preface, xiv),其徒劳程度,堪比历史学家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寻找一个事先存在的、目标明确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
柯特金的论断是颠覆性的:正如“资产阶级”更多是 1789 年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东欧的“公民社会”同样是 1989 年革命的后果而非其主要动因(Preface, xiv)。他犀利地指出,在一个彻底贯彻列宁主义一党专政及其必然产物——国家所有并运营的经济体制——的国度里,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拥有自主资源与公共空间的公民社会根本不具备存在的物质与制度基础。感谢 1989 年对一党垄断及其经济推论的否定,才使得公民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
为支撑这一论断,柯特金对东欧各国的具体情状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与辨析。他承认,波兰的案例最具迷惑性。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存在,以及天主教会提供的强大组织庇护与精神支持,确实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它也的确“将自身想象为公民社会”(imagined itself as civil society)。然而,柯特金强调,正是波兰的这一独特性,使其成为了一个“宏大的例外”(the grand exception),而非普遍的范式(p. 33)。学界的核心谬误在于,将波兰这一特殊案例的经验不恰当地普遍化,套用到了整个东欧。
当我们将目光从波兰移开,便会发现“公民社会”叙事的苍白无力。在匈牙利,1989 年的“圆桌会议”看似是一场政权与反对派的谈判,但柯特金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匈牙利的反对派力量“孤立且人数稀少”,以至于为了能有一个谈判对手,党内的改革派不得不主动去“扶植反共的反对派”(Preface, xiv; p. 10)。而在东德与罗马尼亚,情况则更为极端。这两个国家并未出现任何成气候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然而,吊诡的是,1989 年规模最宏大的街头示威,恰恰爆发在这两个拥有最令人胆寒的秘密警察系统(斯塔西与罗马尼亚安全局)的国度,而非拥有团结工会的波兰(Preface, xv)。这种“非组织的动员”(nonorganized mobilization)现象,本身就构成了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有力反驳。
因此,柯特金的第一个理论贡献,便是将“公民社会”这一被赋予过多规范性与理想色彩的概念,重新置于严格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审视。他并非否定异议分子的道德勇气,而是从结构与实力的层面论证,这些“大部分由少数异议分子组成的小团体”,无论其道德力量多么重要,都不足以构成一个能够撼动整个体制的“社会”(p. 34)。如果说 1989 年的崩溃不是一场由外而内的胜利,那么历史舞台的真正主角究竟是谁?柯特金由此引出了他的核心创见:崩溃的根源,必须到体制的内部——那个他称之为“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的庞大建制中去寻找。
2、“非公民社会”的定义与特征
“非公民社会”是柯特金用以描述共产主义体制下统治精英阶层的独创性概念。它并非简单的“统治集团”或“官僚阶层”的同义词,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学内涵的分析工具。柯特金明确指出:“极权或准极权国家并未消灭社会——它们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社会”。而“非公民社会”这一术语,指的便是“这些伴随一个非自由国家而生的、强大的社会纽带与社会组织形式”(p. 12)。
这个“非公民社会”的成员,涵盖了党务工作者、政府官员、宣传干部、军队与秘密警察的军官等党 - 国精英。它是一个拥有“全套制度、协会、侍从关系及其他网络”的庞大体系(p. 11)。其成员通过特殊的身份认同(如党证)、共享的生命经验(从青年团到党校)、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在罗马尼亚的党校或东德的波茨坦斯塔西学院结下的“同学情谊”)以及一套自洽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个社会内部等级森严,却也分享着共同的特权:优先分配的住房、特供商店、专用医院与疗养地、乃至“坚不可摧的‘军用’手表”(p. 11)。柯特金估计,包括家庭成员在内,这个群体约占各国总人口的 5% 到 7%,它绝非一个孤立的政治寡头集团,而是一个根植于体制、盘根错节的社会阶层。
其“非公民”的本质,恰恰在于它与“公民社会”的各项原则背道而驰。它并非一个由法治所建构、保护和制约的社会,其运行不依靠透明的法律规则,而是仰赖于非正式的权力网络与人情关系——当一个精英的子女遇到麻烦,他会求助于“党务”部门而非法律(p. 12)。它建立在消灭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之上,因而缺乏独立的司法、文官系统和媒体来制衡国家权力(p. 9)。简言之,“非公民社会”是极权主义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物:如果极权主义描绘了一种全方位控制社会的国家形态,那么“非公民社会”就是这种国家形态所催生、并反过来支撑这种形态的那个特权社会实体。

3、“非公民社会”的内在悖论
在清晰地界定了“非公民社会”之后,柯特金进而深入剖析了其赖以生存的体制所固有的、最终导致其“内爆”的一系列结构性悖论。正是这些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使得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实则脆弱不堪。
柯特金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存在一种“负向选择”机制,即奖赏忠诚而惩罚其他一切(p. 15)。为了消除任何潜在的权力威胁,官员们倾向于任命能力较弱者作为直接下属,这种现象自上而下层层复制。具备独立判断和首创精神的个体,通常会被系统性地淘汰或压制。其结果便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平庸化与僵化。更致命的是信息失灵。尽管拥有如斯塔西般无孔不入的监视网络——其档案文件多达 600 万份,监视着 2500 名反对派活动分子(p. 53)——这个体制却无法有效收集和处理关于其国家的基本信息。各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谎报“童话般的故事”,整个系统陷入了“只听到自己声音”的封闭循环,最终丧失了面对现实、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
由于共产主义体制宣称要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动员所有社会成员为其目标服务,它便失去了应对自发性社会冲突的任何“安全阀”或弹性空间(p. 15)。在多元主义社会中,劳资纠纷、民众请愿、媒体批评等都是正常的社会泄压机制。但在“非公民社会”的统治下,任何细微的冲突——无论是工厂罢工、民众对物价上涨的抱怨,还是对一部戏剧被禁的抗议——都可能被视为对体制本身的“生存威胁”。这种将一切社会矛盾都上升到政治对抗层面的做法,使得整个系统变得极其脆弱。
柯特金深刻地揭示了“非公民社会”的吊诡之处:其成员“拥有对几乎所有国家资源的无限权威和支配权,但他们却陷入了瘫痪”(p. 13)。他们可以推动整个农民阶层的集体化,可以实现整个国家的国有化,却在事后发现,当某些事情出错时,他们连采取最轻微的纠错措施都无能为力。这种麻痹状态,源于体制对任何改革的内在恐惧。因为对于一个建立在全面垄断基础上的系统而言,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无论是引入市场机制还是放松政治控制——都无异于“自我清算”(p. 59)。因此,在问题面前,最安全的选择永远是“坚守常规”(p. 41)。
这些内在的悖论,使得“非公民社会”在 1989 年之前,早已陷入了“依赖西方”的窘境。为了维持其对民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也为了弥补其低效率计划经济的巨大窟窿,东欧各国不得不向西方大量借贷,陷入了柯特金所称的“庞氏骗局”(p. 29, 57)。这种对宿敌的经济依赖,不仅在心理上摧毁了“非公民社会”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也为其最终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二、
在精准地界定了“非公民社会”这一核心分析工具之后,柯特金便运用它来剖析 1989 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具体过程。他并未陷入对各国事件的琐碎铺陈,而是以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经济学隐喻——“银行挤兑”——为理论支点,并辅以对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三个典型案例的深度解剖,清晰地揭示了这场历史剧变背后惊人相似的内在逻辑。
1、政治的“银行挤兑”:隐喻与现实
“你是怎么破产的?”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借人物之口问道。“分两步。先是逐渐地,然后是突然地。”柯特金以此名言开启全书第一章“银行挤兑”,意蕴深远。这精准地捕捉了 1989 年剧变的节奏:数十年的僵化与衰败是“逐渐的”过程,而最终的崩溃却是“突然的”雪崩。
柯特金创造性地将“银行挤兑”这一金融现象移植到政治分析中。他指出,银行的稳固,依赖于储户对其偿付能力的信心。即便一家银行资本充足,一旦发生信心危机,所有储户同时提款,银行也必将倒闭。同理,一个极权政权的稳定,同样依赖于其治下的人民(包括精英群体自身)对其拥有维持统治的意志与能力的信心。这种信心一旦动摇,便会触发政治上的“挤兑”: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精英阶层的消极不作为乃至公然倒戈,最终导致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权在极短时间内骤然瓦解(p. 34)。
这个隐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抓住了 1989 年危机的两个核心特征:
第一,信心崩溃的决定性作用。崩溃的直接原因,并非反对派的力量已足以推翻政权,而是“非公民社会”自身失去了维持统治的信心。这种信心的丧失,源于长期的经济困顿、与西方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最关键的——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再进行军事干预。正如柯特金所言:“一旦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规则,(非公民社会)便通过投降——或拒绝投降从而使自身易于遭受政治银行挤兑——来终结自己”(p. 34)。苏联的“存款保障”被撤销了,“银行”的信誉便荡然无存。
第二,崩溃的连锁反应与加速机制。银行挤兑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当一部分储户开始提款,会引发其他储户的恐慌性跟进,形成恶性循环。1989 年的东欧亦是如此。匈牙利开放奥地利边境,导致东德民众经由匈牙利逃往西方;莱比锡的和平示威未遭镇压,鼓舞了其他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波兰团结工会合法化并最终组阁,则向整个东欧的“非公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旧秩序已时日无多。一个个看似孤立的事件,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迅速汇聚成一场席卷整个东欧集团的信心崩溃浪潮。
柯特金强调,在这场“挤兑”中,社会动员的形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化”抗议。在大多数国家,它表现为一种“非组织的动员”(nonorganized mobilization),其动力并非来自某个统一的反对派司令部,而是源于普通民众在特定情境下的自发选择,以及通过“小众圈子”(niches)和朋友关系传播的信息(p. 60)。这正是该理论能够解释为何在缺乏强大反对派的东德和罗马尼亚,同样会爆发大规模街头运动的关键所在。
2025 年 10 月 30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