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燕子:天長地久有時盡,此痛綿綿無絕期——追憶王策先生
人到初老,世事滄桑
從周勍的臉書上得知王策先生歸天的那天正是令和三年(2021 年)元月八日。同一天,我在大阪的一位好朋友也走了。真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痛綿綿無絕期…
人到初老,世事滄桑,似乎寒冬的風都吹進骸骨,月光一拐一瘸,照著我回家的路。
黃河清先生(1946-2014)的介紹
大約是 2007 年或者 2008 年,大陸異議畫家嚴正學先生再次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後出獄歸來,打算創作林昭、張志新者兩位為爭取自由的象徵性女傑的雕像。我的兩位閨蜜姐姐,劉真和柳茵,她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運人士」,但俠膽義腸,熱心為此事募捐。
我曾經郵寄過一本拙著《這條河,流過誰的前身與後世?》給黃河清先生,順便說起此事,沒想到河清先生與巖先生都是浙江人,他也在海外張羅此事。
河清先生來信說,燕子,我以前也畢業於溫州師範學校,也是學校老師,當老師這個職業雖然收入不多,但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生第三樂矣,千萬不要放棄這個工作。有機會來馬德里,我帶你們夫婦到處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
河清先生還為拙著寫了一篇書評,叮囑我「自養自立自強自由最毅宏」,並將我祖父劉念滋的故事收入他正在編寫的《當代中國史稿》,還將我父親(北京大學化學系準右派)的故事推薦給香港五七學社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的武宜三先生,後來武先生編進《1957 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中。
河清先生得知我研究流亡知識人和流亡文學,寄給我《不死的流亡者》,長途電話裡說,燕子,有個不死鳥,叫王策,你一定要認識一下。於是又發來許多關於王策先生的資料。這樣,我同王策先生就有了電郵往來。
王策先生發來他的《中國重生之路》、《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改良案》、《中國共和憲政之路》的電子版來同我「商榷」。(羞愧)
我這一代以及往後的留學生,更多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看破紅塵後的世故。我的「憂國憂民」情節已經被同代留學朋友戲稱為「赤膊上陣」了,沒想到還有王策先生這樣傻乎乎的小白兔,早已獲得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的敲門磚,本來可以用一些矇人「中國問題」躋身於西方學術界,在西方獲得平台和名聲之後再回國當「講座教授」之類,變換一件馬甲,雙贏,通吃,光宗耀祖,陶醉于無聊的學術應酬和吹捧,酒飽飯足之餘進行一些所謂「友好活動」,從利益共同體中分得一杯「合作研究」的殘羹冷炙。何況,他並非因被動流亡而出國,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是中山大學的青年講師了。這麼一個人,卻不自量力地飛蟲撲火,自己跑進去想上書全國人大「中國三十年的政治改革方案」而坐了四年牢。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前面還有醫學博士王炳章也是義無反顧地自願跑回去坐牢。
這些赤誠的海外學子「單純得就像真理一樣」。
我曾經用「天生一株向日葵,那滿腔的虔誠生長到最高處」來形容日本「六八代」對理想的執著和獻身精神。但在時代的巨變和遺忘的風中,大家都做了馬後炮,將他們這一代人的價值和命運當做剔牙縫時的談資笑料。
認識王策先生和「不死的流亡者」們,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人中為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而勇敢獻身的人,尚未滅種,他們在石縫中仍然頑強地發出自己微弱的聲音,可惜對岸裝聾作啞或者完全抹殺。
「燕子,你的研究,是時代的見證,你要堅持下去」。王策先生鼓勵我。
所以,到今天,我還在兩條腿的行走,教書和研究,尚未停止,得益於兩位溫州兄長。。
2010 年的西班牙之行
2010 年的 8 月,我們決定去歐洲旅行。
先到德國,在法蘭克福承蒙費良勇先生和海霞的接待,他們夫婦準備了一輛床車,拉著我們到處跑。然後我們轉搭 ICE 列車南下慕尼黑,周勍帶我們在慕尼黑大學蕭爾兄妹廣場呆坐,任夏日的陽光如白玫瑰般地綻放臉上。
王策先生開車載河清先生來機場迎接我們。我給王策先生帶去一件中古的紫色的和服,他找了一個大衣架掛在店內作擺設。
隨後,茉莉、傅正明夫婦從瑞典、另外一位女友從英國趕來跟我們相聚。
王策先生幫我們預約了一間乾淨又可人的小旅館,因為河清先生一再囑咐他,日本人愛乾淨,燕子不是我們這樣吃得起苦的人。總之,先給王策先生上了一堂日本人如何如何的課。
結果他跑了好幾家旅館,每家都親自去實地察看是否「達標」。

白天我們一群人出去遊山玩水,回來就在他們兩家吃飯。河清嫂則從郊外趕回來送菜,烹調。王策先生的女兒依依有時來陪我們。
河清先生在《迎接日本劉燕子諸友來訪賦詩記之並序》中記錄:「大病初癒,不敢移重,體弱氣喘,費時三日,將雜亂局促不能再雜亂局促之斗室重新編排一番」,並賦七律一首。
傅正明先生和詩,《拜謝河清王策仁兄款待》,王策先生亦「依韻繼聲」
「神州淪落奈何天,弱女來擔道義肩。飛燕憐銜海上石,莉花怒放火中蓮。卅年愧上天人策,今日羞參文字禪。斗室沾花吾何幸,眾生有病望療痊。」


茉莉姐與河清先生只要在一起,無時無刻不在「憂國憂民」,談論時政,針砭時事。有時各自固執己見,爭得面紅脖子粗。王策先生微笑著從中調和。
我敬佩這一代人的率真,誠實,流亡者的痛苦,在於真誠地愛國。
下一代海外留學、打工甚至技術性地流亡,大都是機靈鬼,他們會將自己藏得滴水不漏,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如果把中國比喻為一條患了癌症的的胳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切掉這條有血有肉的胳膊,移植一條沒心沒肺沒感情的機器人胳膊,絕對不想去醫治,更不會去為如何醫治而傷腦筋。
誠如胡平先生在《為理想而承受苦難》中說的:
「流亡者是難民,但又不單純是難民。單純的難民只是為了躲避對自己的迫害,一旦進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為流亡者,在於他們總是執著地關心著自己的命運—不論是在政治的方面或是在文化的方面,並且還熱切地希望在其中發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雖然因為躲避迫害而離開祖國,但是他始終認為自己的事業在祖國,自己生命的意義在祖國;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於迫害,但是從此也就將他的靈魂撕裂成兩半」。(《不死的流亡者》頁 149)
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裡,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到了西班牙,才真正明白了這個道理,憑一口溫州話的熟悉腔調,就可以找到鄉黨,可以找到一個飯碗,但卻難以找到同志和朋友。
王策先生的小雜貨店開在華人街,從小超市,洗頭店,洗衣店等等到處都是溫州人的一條龍服務,不需要西班牙語完全可以魚兒一樣自由地生活。他去的也是溫州同鄉多的華人教會。但是同他談得來的人似乎寥寥無幾。
那時王策先生已經出獄六年,人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但看得出他的苦悶和困境。
在自由世界,沒了恐懼,沒了危險,但是沒有幾個西方人來關注他的政治理想,就像行俠仗義的堂吉訶德,跟風車激戰,儘管這是「正義的戰爭,消滅地球上這種壞東西是為上帝立大功」,但由於堂吉訶德不會折服於現實,改弦更張,他雖然視死如歸,勇往直前,人們一邊讚頌這種除暴安良的經典的騎士精神,一邊又嘲笑他的過時,糊塗。
其實,真正應該嘲笑的,何嘗不是我們今日所處的「ろくでもない世界」呢。(他媽的世界)
他的內心仍然懷有熾熱的抱負,就像一位步法、計時、手速都準備好的拳擊手,卻一拳擊中在棉花上,無力,失落,徘徊在絕望的邊緣。
他成日枯坐在小雜貨店裡,對做買賣也不熱心,常常關注網上的時政。

那幾天,我們幾位女性抱定當「母大蟲」顧大嫂的決心,進來一位客人就演「櫻花戲」,絕不讓他空手走人。
夏日的馬德里,週末的傍晚,有各種各樣的露天音樂會,歌劇表演。
河清先生每次來,都非常紳士,給我們每位女士送一支紅玫瑰。我們一夥還去看了西班牙的佛朗明哥舞蹈,最後在一家簡易的四川小餐館裡告別。
那天,王策先生好像特別高興,伴隨著哄哄的油煙味和吱吱的電風扇片的噪雜音,敲著筷子吟唱《滿江紅》。情調激昂,慷慨壯烈,那種無私無欲,壯志未酬,渴望征戰沙場的遠大抱負,跟平時那種儒雅寡言,在小雜貨店坐成「化石的糟老頭」(他自嘲)判若兩人。

在大阪哲學學校講座
兩年後,友人邀請我合著一本日文書,關於國內外矢志不移,堅持自由民主人士的故事。友人撰寫三十年民運史和劉曉波、陳光誠的部分,我則寫了王策、茉莉、余杰、冉雲飛等人。這本書被出版社取了一個吸人眼球的書名《反旗》。
正好王策先生到東京參加民運方面的會議,他很高興這本記錄他人生歷程的小書出版,在東京逢人就推薦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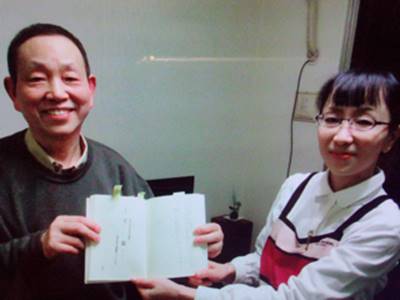
我和家人邀請他乘新幹線南下,還找了一位主攻中日近代史的朋友一起陪他遊覽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名勝古跡,尤其是明治維新期的志士仁人足跡。
我還聯繫大阪經濟大學的哲學教授平等文博先生,他們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哲學研究會—「大阪哲學學校」,還擁有自己的季刊《唯物論研究》和通訊會報,會員中有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者,有啟蒙辯證法的研究者等等,總之,麻雀雖小,群英薈萃。
平等教授很快回信,歡迎王策先生去給他們舉辦一場特別講座。
那天,大阪哲學學校的老校長,著名的社會思想史以及哲學專家,85 歲高齡的山本晴義老教授、季刊主編、康德的研究者田畑稔等人都來參加了講座。
王策先生談的還是他心心念念的中國浴火重生之路以及中日近代史中對日本中國革命的支持。會後山本、田畑等人與他又熱烈地討論起作為方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自由人聯合體」在冷戰後的意義等等。
那次討論會從下午兩點到七點,之後又承蒙諸位學者的招待,到附近的居酒屋小酌,幾杯燙過的清酒下肚,惺惺相惜,他鄉遇知音。
王策先生在電車上跟我說,沒想到日本還有這麼多理想主義者。

息了地上的勞苦,享受天國永遠的福樂。
2018 年,我們去溫州,王策先生的大姐王希坐著公交車來機場迎接,不顧高齡,幫我拖大行李箱。我們就住在大姐的家對面的旅館。
大姐家的客廳掛著弟弟「鐵筆」(獄中製作的)寫的對聯。鄭大同老師(他是向王策先生傳福音的第一人)也來了,大姐親手做溫州小吃給我們品嘗。大姐回憶起 1998 年 -2002 年探監的情況,那時王策的太太和其他兄弟姐妹離得遠,大姐就承擔起每月探監的任務。
王策先生回歸天家後,在微信上,王希大姐說,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弟弟是最小的,沒想到,弟弟走在我前面。拜託我轉達作為親人,感謝弟弟的所有朋友。
我回信:大姐,王策先生是中國人的驕傲,溫州人應該為他感到自豪,他改變了世人對溫州人只管埋頭賺錢,不問國事的看法。他知行合一,在理想裡安身立命。他不過息了地上的勞苦,享受天國永遠的福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