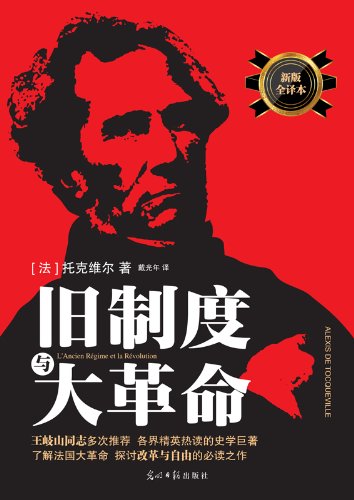
赖建平:论反政府权(七)——改良中的专制政体下革命权的限制
任何专制或威权政体,一旦启动了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良,其人民的革命权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人民无权发动大规模的集体革命行动,只能以个体革命的形式采取局部的实际行动。但人民有权进行集体革命的宣传、酝酿,为此做准备,以便保持政治压力,在统治者停止改良甚至倒退时立即付诸行动。实质性改良最少包括两个条件:(1)最高统治当局已经做出了进行宪政民主改良的正式决定,形成了相应的系统性权威文件,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实施;(2)人民已经拥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除非实质性改良已经启动,否则革命权丝毫不减;一旦实质性改良已经启动,革命权立即中止。这应该成为一条普遍的有关革命的道德原理。
一、改良与革命都是推动政治进步的基本方式
毫无疑问,改良与革命是人类政治进步、制度优化的两种基本方式和途径,分别由统治者自上而下以和平方式进行或被统治者自下而上以暴力方式展开。在历史长河中,各国、各民大多数时间保持和平与秩序,以改良求进步,只有少数时间经历战争与内乱,以革命求突破。“人类历史上的进步大概不外是通过两条途径,即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和改良(以和平的方式)”【《法国革命论》译者序言第 10 页】
改良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可欲;革命仅仅是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不可欲。但二者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革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的物质力量,当它引而未发时,则是革命的威慑。没有摧毁性的革命行动便被不可能有革命的威慑,没有威慑,就没有压力,从逻辑上、道义上全面否定革命权,那任何改良都不可能发生,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放弃既得权力。改良可以没有动力,但绝不可以没有压力。可能会催生、促发革命、正在酝酿革命、已经开始尝试革命等等情形都是足以迫使统治者改弦易辙的革命压力。那种排斥革命,将革命污名化的取消革命论荒谬且有害。
与来自被统治者的外部压力相对,还存在改良的动力,它来自统治者内心,是统治者自我内在的意志决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样,都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人,都有道德性,都同时存在作恶、为善的可能。既有自私残暴、冥顽不化的暴君、独夫,也存在相对温和仁厚,追求卓越的开明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既有利益冲突的一面,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面,既矛盾、斗争又合作、协调。结合环境与条件,统治者既可能加强集权、加紧奴役,也可能简政放权,进行政治改良。那种认为一切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进行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只有革命一条路的迷信革命论同样是荒谬的、有害的。如果该论点成立,那就意味着政治改良是一个伪命题,人类一切的制度改进无一例外地都必须是你死我活的内战的结果,暴力革命成为政治进步的唯一动力。这显然不合事实。“和理非”与“革命派”各执一端、排斥对方的争论不得要领。
二、革命是无奈的选择、最后的手段
政治暴力是把多刃剑,它是潜在暴君抢班夺权的根本途径,是现存专制统治者维护独裁统治,压迫、奴役人民的基本工具,也是民主社会的人民进行政治自卫,防止政府腐化变质的坚实后盾,还是被压迫人民求解放、争自由的终极手段。
作为工具的革命,技术可行性另当别论,仅就道德可欲性而言,它只能是最后的手段,能改良、不革命,这是一条根本原则。革命除了会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社会动荡、失序、混乱等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不可欲的后果以外,即使付出如此巨大的社会代价,仍然很可能事与愿违,革命的预期后果无法实现,甚至革命后新建立的政权远比被推翻的政权更加残暴,播龙种、收跳蚤。
作为革命对象的政权,犹如无主野兔,谁都可以竞逐,猎为己有,革命的公益目的经常被野心所激发出来的私利、权欲所异化,革命很可能沦为极少数革命领袖人物争权夺利的角斗场,很容易导致不断变更革命对象、没完没了、你死我活的过度革命,出现破而不立的乱想。在任何社会,多数人都贪生怕死,既不敢施暴,也不敢抗暴,极少数歹徒、强盗常常可以轻易控制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群体。多数人更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参与革命。这就意味着,一场革命可能代表了多数民意,是那些不敢参与者所乐见的,但也完全可能是少数亡命之徒的铤而走险,这样的暴力革命无论从发动到可能取得的胜利,其实都只是少数意志的体现。此时的革命者由于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往往会在革命成功以后要求获得超额的血酬回报:垄断政权,专制统治,革命沦为改朝换代的闹剧。
无论原政权如何不堪,一旦它愿意进行政治改良,这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质变。它可以克服革命可能只是少数意志的体现这一弊端,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意志公共化或谓公意最大化,最可能且破且立,顺利完成新旧制度的转轨与衔接。因此,和平改良在道德上可贵、可欲,作为一种追求政治体制进步的技术手段,其有效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那些皇权思想深重的国度。改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革命只是改良无望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三、托克维尔命题之性质与启示
改良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自由与权利的重大调整与重新分配,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此消彼长,政府必然要放松对民间的管制,给与人民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间,它会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局面:改良越深,革命越易。改良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削弱政府权威,扩大新闻、言论、结社等自由空间,同时大幅度提高人民期望值,降低人民忍耐度与怒点,从主客观两方面都使得革命更加容易。此时如果人民利用改良给革命提供的方便而发动革命,它正当吗?
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或称之为悖论:改良常常导致革命。他说:“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氏描述的是一种很可能但非必然的实然现象,他只是从现实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具体实例中进行不完全归纳所得出的或然结论。事实证明,人类很多改良都很成功,没有导致革命。革命既可能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也可能在那些人民感受最绝望的地方发生,改良可能引发革命,也可能消除革命。如果事实证明一切改良都必然导致革命,那改良就是主动找死,就会绝迹,任何专制统治者都只会抗拒到鱼死网破。对于专制国家的人民应不应该利用改良所提供的条件发动革命这一个应然问题,托氏没有明确阐述。
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不是被决定的单向必然性,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集团之间的自由博弈关系,改良到底消弭革命还是引发革命,是由双方的博弈策略决定的。统治者无论基于何种情势而开启改良的闸门,其根本动机当然是消除而非触发革命。但一旦做出改良的决定,统治者的策略就很难改变,主动权更多地转移到了被统治者一边。后者通常有两种选择,或以善意对待善意,信任对方,双方合作,在斗争中贯彻妥协主线,最终顺利达成改良目的,革命的动因消除;或者利用改良所提供的放松社会管制的契机,发动革命,推翻统治者。这时,被统治者的策略选择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窃以为,在任何其人民享有革命权的社会,一旦统治者开始了实质性政治改良,被统治者就不应该再进行以推翻原政权为目的的大规模集体革命,也即此时的革命没有道义正当性,属于非法革命。
利用改良搞革命是一种以怨报德。无疑,主权在民,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任何专制统治者都没有权力统治人民,终结其统治天经地义。但是,任何现存统治都具有特定的历史渊源,统治者主动还权于民、还政于民总归是一种善意,在政治上、道德上是难能可贵的,并不是所有的强盗都愿意返回赃物,直到今天,众多大小独夫民贼还在一如既往地统治着,人们仍然束手无策。
如果统治者改良,人民仍有权革命,就意味着它和原地踏步的继续专制、倒行逆施加紧专制在政治道德上没有区别,对统治者的评价、对待他们的行为方式相同,这是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成王败寇,一切都是实力问题,抱残守缺的顽固派与革故鼎新的改良派,在道德上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是不公正的。
如果改良得不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甚至反而乘势搞革命,那就没有任何统治者愿意、敢于放松管制,再大的内外危机都不能让它后退半步。改良必然就是找死、速死,相反,非但不改良,反而变本加厉,勒紧绞索,最多也就是等死。任何统治者的寿命都是有限的,都想确保不会在自己当政期间因放松管制而遭遇革命,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只能将危机尽力无限拖延,成为统治者之间击鼓传花的危机推诿。
不妥协的极限专制统治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拧紧的弦迟早会有绷断的时候,到达一个极限,必然会发生鱼死网破的革命。此时的革命代价将极其巨大,社会崩溃失序,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摧残,血流成河近乎必然。这样条件下发生的手段革命往往很难实现目的论意义上的革命结果,也即很难顺利实现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一革命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