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东云:反腐亡党亡国,不反腐也亡党亡国(上)
长期以来,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崛起,西方学界与公共舆论场中一度流行着一种关于“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迷思,这种叙事试图构建一种幻象,即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坚持列宁主义的刚性垄断,但在经济治理与自我革新上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性与高效能,仿佛它成功地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嫁接在了一党专制的政治躯体之上,从而走出了一条超越历史终结论的独特道路,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则毫不掩饰地直接提出了所谓“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头一个就是道路自信。
我最近终于找出了时间读了一遍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 2016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出卖中国:中国官场贪腐分析报告》(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读完之后,我又去看了一遍他今年年初发表的论文《从整肃到控制: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近期转向》(From Purge to Control: A Recent Pivot in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rackdown),觉得追寻所谓中国模式的来源、特征与未来,“腐败 - 反腐”确实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出卖中国》一书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当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并非经济改革伴生的意外副作用,而是 1989 年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之后,中共为了维持政权生存所做出的制度性选择的必然恶果。作为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中共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短缺乃至危机,为了换取统治集团内部的忠诚与凝聚力,同时也为了推动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中共不得不与官僚体系进行了一场交易。这种交易体现在两个关键的制度变迁上:一是行政权力的下放,尤其是人事任免权的层层下放;二是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不彻底性(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正如裴敏欣在书中所深刻洞察的,这种独特的“混合经济”体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土地、矿产、国有企业等核心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名义上仍归国家(即全民)所有,但其实际的控制权与处置权却被下放给了地方党政官员和国企干部,使得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得以通过勾结(Collusion)的方式,将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矿产与企业资产,在缺乏法治约束的黑箱中迅速变现为巨额的私有财富。不同于早期散兵游勇式的个体贪污,1990 年代以后的腐败呈现出鲜明的“窝案”、“串案”特征。官员、商人、甚至黑社会成员,基于共同的利益捆绑,形成了排他性的掠夺网络。这种网络不仅用于分赃,更用于在体制内互相掩护,以此抵御来自上级的监督和法律的制裁。这种“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的形成,实际上标志着权力的私有化与黑帮化,而国家机器在这个过程中,也退化为了单纯的自利集团。
然而,当我们站在 2025 年的今天上重新审视这一论断时,必须引入裴敏欣在《从整肃到控制》一文中的最新观察,才能理解这种衰败(Decay)究竟已经演进到了何种程度。根据裴敏欣对官方数据的梳理,在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整整十二年后的 2024 年,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创下了历史新高。2024 年前九个月即有 88.9 万人被处分,按年化计算将达到惊人的 118.5 万人,这一数字几乎是 2023 年的两倍,更是运动初期 2013 年的六倍有余。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反腐悖论”:如果这场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严厉的清洗运动是有效的,那么腐败的存量应当减少,被惩处的人数应当呈下降趋势。裴敏欣在论文中指出,这种异常的增长并非单纯反映了腐败的猖獗,更反映了习近平政权在清洗了周永康、令计划等显性政治对手(即“整肃”阶段)之后,为了应对独裁者内心那种“不可治愈的不安全感”(incurable insecurity),而将反腐运动的重心全面转向了对官僚队伍的绝对控制。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 年、2018 年和 2023 年三次修订)的文本分析,以及对 2023 至 2024 年间大量中高级官员处分案例的实证考察,裴敏欣指出,现在的中共正在通过不断扩充“违反政治纪律”和“违反组织纪律”的定义,将从前属于思想认识、私人生活乃至消极怠工范畴的行为,全部纳入惩戒的射程。诸如“妄议中央”、“结交政治骗子”、“破坏政治生态”以及“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互联网资讯”等模糊且口袋化的罪名,已经成为了悬在每一位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据分析显示,“对抗组织审查”已经成为清洗官员最强有力的程序性武器,大约 30% 的高级官员和高达 77% 的中层官员在落马时都背负着这一指控。这表明,当下的反腐已经超越了《出卖中国》中所描述的打击“权钱交易”的经济逻辑,进化为一种旨在粉碎官僚体系内部任何潜在的“攻守同盟”与“独立意志”的政治规训工程。
《出卖中国》揭示了中共如何因为贪婪而不仅出卖了国家资源,更出卖了其组织原则,导致了“经济性的腐烂”,而《从整肃到控制》这篇论文则向我们展示了中共如何因为恐惧而陷入了“政治性的坏死”。习近平试图用极其严苛的纪律工具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留下的烂摊子,试图用对领袖的绝对忠诚来替代利益分赃的凝聚力,但其结果却是制造了一个更为棘手的困境:官僚体系在无所不在的监控与清洗威胁下,陷入了普遍的瘫痪”与“躺平”,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空心化。这种依靠恐怖维持的稳定,比依靠分赃维持的稳定更加脆弱且不可持续。当公共财富被瓜分殆尽的危机尚未解决,新的政治高压又切断了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时,这个看似庞大的利维坦,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自身逻辑所铺就的死循环中,正加速滑向历史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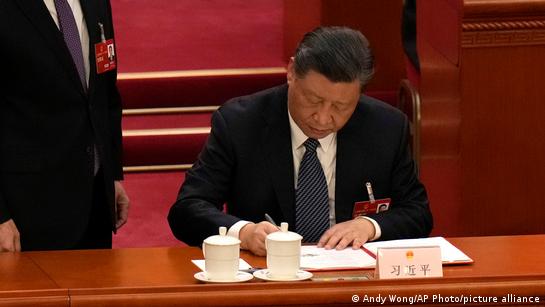
如前所述,经过了 1989 年的武力镇压、1991 年的苏东巨变和 1992 年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在一个列宁主义政体中引入市场机制以维持生存,刻意制造了一种扭曲:一方面是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不完全性”与“渐进性”,另一方面是行政权力(特别是干部人事权)的“激进下放”与“去监管化”。这两个维度的交汇,构成了滋生权贵资本主义最肥沃的土壤,它使得公共权力与公共资产的结合不再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而是为了在缺乏法治约束的黑箱中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性交易,这种交易的规模之大、渗透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都实属罕见,它标志着中共政权性质从革命党向“掠夺型国家”的根本转变。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中国所谓“渐进式改革”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特别是产权改革的致命缺陷。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清晰界定的产权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产权的模糊性恰恰是统治精英维持政治控制与攫取经济利益的必要条件。1990 年代以来的改革,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抛弃了计划经济的教条,但在所有制结构上却坚守了“公有制主体”的底线。这看似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实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掠夺机制。国家保留了土地、矿产、大型企业等核心资产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在法律上属于全体国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国家却将这些资产的“控制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大规模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剥离,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委托 - 代理难题:作为名义所有者的“人民”缺位且失语,而作为代理人的官员却拥有了类似封建领主般的支配力。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这种剥离可以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透明的审计制度和自由的媒体监督来制约,但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这一切都不存在。因此,这种产权安排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无主资产池”,而掌握审批权的官僚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将这些公共资产的控制权在形式合法的掩护下转化为私人收益,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产权模糊性在土地制度的演变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这也正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最血腥、最暴利的领域。我们在阅读裴敏欣关于土地权力的章节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掠夺合法化的路径。从 1980 年代末《宪法》修正案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到 1998 年《土地管理法》的确立,中国政府在法律上确立了国家对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及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绝对权力。这种制度安排赋予了地方政府双重身份:它既是土地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又是唯一的土地供应者(通过征地)和最大的获利者(通过出让)。这种“独家垄断”地位,结合了不受制约的行政裁量权,使得地方官员拥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他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强拆和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将土地从“集体”手中征收上来,然后通过操控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在招拍挂程序中设置排他性条件,将这些土地以某种“协议价格”转让给与自己有利益输送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尽管习近平时代强调“房住不炒”,但在财政分权体制未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依旧的背景下,这种掠夺机制只是变得更加隐蔽。裴敏欣在 2025 年的论文中提到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之所以屡禁不止,正是因为官员们依然掌握着对土地和基建项目的绝对支配权,他们通过这些庞大的工程将公共财政转化为政治资本和私人利益。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将代际财富和底层民众财富向极少数权贵阶层进行逆向再分配的机制,它不仅造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更成为了官商勾结最主要的温床,即便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今天,其留下的债务黑洞和金融风险依然在吞噬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改制浪潮中。裴敏欣在书中对 1990 年代中后期“抓大放小”战略的分析,揭示了另一场惊心动魄的财富转移。如果在土地市场上是政府作为卖方在掠夺,那么在国企改制中,则是内部人(国企高管与主管部门官员)作为买方在进行自我掠夺。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资产评估机制和竞争性的拍卖市场,所谓的“改制”往往变成了“内部人私有化”的代名词。官员们可以通过故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虚构债务、或者将优质资产剥离到自己或亲属控制的影子公司,将数十年积累的庞大工业资产以白菜价据为己有。这种掠夺之所以能够得逞,关键在于产权改革的“不完全性”——即允许国有资产进入市场交易,却不允许市场来决定资产的价格,价格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拥有行政审批权的官员手中。正如书中所论证的,这种改革模式并非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为了提高效率,其深层动力在于它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提供了一个瓜分旧体制遗产的机会,从而换取了他们对政权转型的支持。这种通过出卖国家利益来购买精英忠诚的策略,是后极权主义政权维持生存的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它虽然暂时稳固了统治联盟,却从根基上腐蚀了国家的肌体,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变成了一个以逐利为唯一目标的自利集团。而在裴敏欣 2025 年的论文中,我们悲哀地发现,习近平虽然在反腐上口号喊得震天响,“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但在制度建设上却完全背道而驰。他不仅没有通过私有化或法治化来厘清产权,反而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战略,进一步扩张了国家(实则是党和官员)对经济资源的垄断。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扩大了官员可以寻租和掠夺的资产池。当更多的资源被集中在缺乏透明度的国企和政府手中,而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时,权贵资本主义的土壤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变得更加肥沃。
仅有产权的模糊和资产的庞大并不足以导致如此普遍且有组织的腐败,另一个关键的拼图是行政权力的结构性变化。1984 年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场改革中,中共将原本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层级从“下管两级”收缩为“下管一级”,这意味着省级、市级乃至县级党委书记(即所谓的“一把手”)获得了对其直接下属近乎绝对的任免权。在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对官员政治生命的掌控权是最核心的权力。当这种权力被下放并集中在地方“一把手”手中时,实质上就在党内形成了一个个封建领主式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不再仅仅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而是掌握着辖区内所有官员前途命运的“土皇帝”。这种权力结构的剧变,彻底改变了官僚体系内部的激励机制。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或保住职位,必须向拥有任免权的“一把手”进行利益输送,这就形成了裴敏欣所描述的“纵向勾结”的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拥有人事权的“一把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升迁),也需要下属在土地审批、工程发包、司法判决等具体事务上予以配合,这就形成了一种基于人身依附和利益交换的共谋关系。
此外,这种制度安排也对官员的行为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产权的不安全性和政治前途的不确定性,官员们普遍产生了一种“末世心态”,并倾向于进行短期行为。既然权力来源于上级的任命而非民众的授权,既然手中的权力随时可能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动而丧失,那么最理性的策略就是在在任期间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将手中的权力变现。这种心态加剧了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无论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招商引资,还是透支未来的土地财政,其本质都是官员为了在有限的任期内最大化寻租收益而牺牲长远的公共利益。裴敏欣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这种掠夺行为往往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以“窝案”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因为在缺乏法治保护的地下交易中,只有通过共同犯罪纳投名状,建立起荣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并规避政治风险。而在习近平三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将“政治纪律”的网越收越紧的当下,官员们一方面为了规避政治风险而变得极度避险,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为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他们必须寻找更强大的政治靠山(即论文中提到的“政治攀附”),而维持这种依附关系需要更巨额的资金输送。因此,腐败不再仅仅是为了个人享受,更是为了支付昂贵的“政治保险费”。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反腐高压下,涉案金额反而越来越大,因为腐败的成本在上升,官员必须通过更疯狂的掠夺来对冲政治风险。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种政治高压,并没有改变官员的掠夺本性,只能让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更加扭曲。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