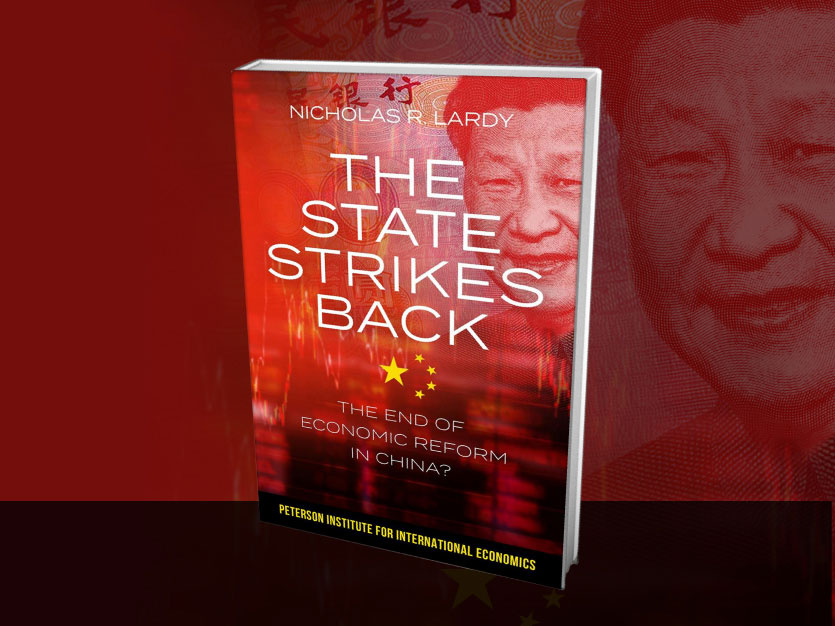
钟经观:国进民退——Nicholas R. Lardy “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读后(二)
在市场里,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如果经营不善,赚不到钱,资不抵债,老板就要关门,就要跳楼,企业就要破产,这是硬约束。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国企的目标函数不是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是资产回报率最大化。它们的目标是什么?Lardy 给出的答案是:“做大”。对于国企管理者和背后的官员来说,规模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本。企业越大,控制的资源越多,能安排的人就业越多,这在官场上的分量就越重。至于赚不赚钱?那是次要的,反正亏了有财政补贴,有银行输血,有垄断地位撑腰,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2012 年以后,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国企兼并案。Lardy 在书中列举了国资委主导的一系列“拉郎配”。把两家本身就效率低下的央企,通过行政命令合并成一家更大的央企。这种合并不产生任何化学反应,既不裁员增效,也不剥离不良资产,唯一的成果就是造出了一个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在《财富》500 强榜单上占个位置。
这种“做大做强”,在经济逻辑上当然是完全说不通的,它不仅没有解决效率问题,反而因为垄断力量的增强,进一步恶化了市场环境。Lardy 的研究表明,这些合并后的巨型国企,其财务表现往往比合并前更差。大量的资金被埋进了回报率极低甚至为负的僵尸国企中,这些资金本可以流向更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创造出数倍的财富。这不仅会造成当下的损失,还是对未来的严重透支。这种由行政权力主导的资源配置,硬生生地在经济机体中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效率剪刀差”,一边是嗷嗷待哺却求贷无门的民企,一边是资金泛滥却效率低下的国企。这种结构性的扭曲,正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跌落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往往就会有人跳出来为国企辩解了,比如说它们承担了若干若干社会责任,无论是稳就业还是在偏远地区提供服务等等,所以效率低是应该的。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充满了“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面纱。而 Lardy 在这本书中则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指出,所谓的“社会负担”——比如企业办社会、退休职工养老等——在 90 年代末的那轮改革中已经剥离得差不多了。至于说国企所在的行业特殊,比如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或者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Lardy 也一一做了证伪。他拿钢铁行业举例,同样是炼钢,同样面对市场波动,私营钢企能赚钱,国有钢企却亏得底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问题不在于行业,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所有制本身。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因为它们承担了什么神圣的使命,而是因为软预算约束,它们的管理者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它们的决策逻辑是政治的而非商业的。当一个企业知道无论亏多少钱都有国家兜底,都有银行续命时,它哪里还有动力去提升效率、去技术创新?
Lardy 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他通过严谨的测算告诉我们,如果能把国企的资产回报率提升到私营企业的水平,中国的 GDP 本可以每年多增长相当可观的百分点。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这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潜力。所谓的“潜力”,就是只要你把束缚在人们手脚上的绳索解开,只要你让资源从低效的地方流向高效的地方,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但在 The State Strikes Back 所描述的那个时间段里,也就是 2012 年之后的几年,我们看到的是绳索越捆越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因为潜力耗尽了,而是因为体制的阀门被关小了。Lardy 用数据证明了,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在一个资本依然稀缺、人均收入依然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任由庞大的国有资产低效空转,这在经济学上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或许有人就要问,既然账算得这么清楚,既然国企低效、民企高效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为什么执政者还要执迷不悟?Lardy 在书中也给出了他的答案,虽然用的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但背后的政治逻辑却呼之欲出。在中共一党独裁的体制下,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这绝非是最高目标,更不是唯一的目标。对于中共而言,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更是其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党控制国家命脉的抓手,是安插干部、调配资源的工具。如果让私营企业彻底主导了经济,如果资源配置真的全由市场说了算,那么党管什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追求使得他们在面临增长放缓的压力时,本能的反应不是放权让利,而是收紧缰绳,他们宁愿要一个增长慢一点但完全听话的经济,也不要一个增长快但他们觉得难以控制的经济。每一次国企投资占比的上升,都意味着无数家民营企业的萎缩甚至死亡,而每一个国企 ROA 数据的下降,都意味着巨额的社会财富被无效地挥霍。为了维护一个小集团的统治安全,可以随意牺牲亿万国民的福祉,难道这就是“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吗?
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共体制内的各级决策者,还是某些依托体制吃饭的官派学者,都在不厌其烦地向外界兜售一套关于国企改革的宏大叙事。他们发明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词汇:“公司化治理”、“做大做强”、“混合所有制”、“债转股”等等。听起来,似乎只要按照这个方子抓药,那些沉疴遍地的国有企业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既有国家战略担当、又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然而 Lardy 的研究工作却告诉我们,所谓的“国企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表演,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老问题,也不是为了理顺产权关系,本质上还是为了在不触动体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行政手段维持国有经济的庞大体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通过行政垄断和要素汲取,制造了更难以撼动的新顽疾。毕竟,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规律是不听共产党的话的,违背了产权界定清晰和自由竞争这两个基本原则,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无法真正“做大做强”一家企业,私企是这样,国企更是这样。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公司化”(Corporatization)。按照 1994 年《公司法》的设想,国企走向现代化,就是要把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引入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最终实现政企分开。然而,Lardy 在书中指出,这不过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法律游戏。直到 2016 年,中央层面的国企改制仍在推进,但这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变更,这种改制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控制权归属。在市场经济中,董事会的核心职能是选聘和考核管理层,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中国的央企里,董事会更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真正的老板是中组部。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由党组织任命的官员,他们关心的首要指标不是资产回报率,而是政治忠诚度和在官僚阶梯上的晋升。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出的企业管理者,难道我们应该指望他们能像在私企当中一样去精打细算、去创新、去冒险吗?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公司化改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但国企的资产回报率却在持续下降。这种只做表面文章的改制,不仅没有切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反而让这种干预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商业外衣,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监督。
第二,国资委主导下的央企大合并。2012 年之后,中国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合并浪潮,南北车合并、中远中海合并、宝钢武钢合并,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央企的数量从成立之初的近 200 家一路缩减到不足 100 家。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这是为了“减量提质”,减少“恶性竞争”,通过合并来打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队”。这种逻辑听起来当然很美好,和把两个胖子捆在一起然后指望能诞生出一个健美冠军的幻想一样美好。
Lardy 在书中分析了南北车合并、宝钢武钢合并等案例,发现这些拉郎配式的合并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升。相反,随着央企数量的减少和单体规模的膨胀,其资产回报率不升反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需要走得太远,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仍然足以解释。这种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合并,其本质是消灭竞争,而竞争,哪怕是激烈的价格战,恰恰是市场发现价格、逼迫企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竞争,消费者才能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服务,资源才能流向那些经营得更好的企业。这种所谓的改革,真可以说是倒着往回改,往计划经济改的改革。利用行政力量去对抗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严重干扰市场上最宝贵的信息机制,也就是竞争价格,导致整个行业的成本不降反升,而这一切的代价,最终都转嫁给了下游的民营企业和无数的消费者。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并购是为了产生协同效应、降低成本或获取技术,而在国资委的指挥下,并购往往是为了消除同一行业内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为了掩盖某些企业的亏损。当一个行业只剩下一两家巨头时,它们就不再需要通过提升效率来争取客户,只需要利用垄断地位进行寻租,或者利用巨大的体量来勒索银行的信贷支持。这种“做大”的过程,实际上是把分散的风险集中化了,造就了一批“大而不能倒”的怪兽。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把两家甚至多家本该互相竞争的企业捏在一起,对内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对外则引起了全球贸易伙伴的警惕和反弹,唯一的收获似乎就是在纸面上造出了一些资产规模惊人的巨无霸,让几家央企在《财富》500 强的排名上能够往前挪动几位。
再来看被寄予厚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Mixed Ownership)。这大概是近年来最具欺骗性的口号之一。按理说,引入民营资本,能够改善国企的治理结构,提升效率,但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概念在执行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异化的。Lardy 详细剖析了中国联通(China Unicom)等“混改”标杆案例。表面上看,那是引入了腾讯、阿里、京东等民营资本,似乎是把民营企业的活力注入了国企的肌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的实质——也就是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究竟有没有发生转移?Lardy 发现,在这些所谓的“混改”案例中,民营资本虽然进来了,真金白银也掏了,但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话语权,甚至连退出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国企的控制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党政任命的干部手中,企业的经营方针依然要服从于国家的宏观战略而非股东的利润回报。对于国企而言,混改更像是一种融资手段,目的是在不丧失控制权的前提下,利用民营企业的资金来缓解债务压力。
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私人的钱被用来填补国企的亏空,或者被用来支持国企的扩张,但私人资本的所有者却无法对这些钱的使用说“不”。产权这一概念当中的另一重重要意涵就是“排他性的权利”。如果我出了资,却不能控制资产,不能决定经理人的去留,甚至不能决定分红的比例,那么这种所谓的“股权”,本质上就不是产权,而是一种被强制征收的“税”,或者说是一种带有政治摊派性质的“捐款”。这种“混改”,实际上是公私合营的现代变种,它是想利用私企的资金来为国企续命,而不是真正想让市场机制在国企内部生根发芽。这种做法,短期内或许缓解了国企的资金饥渴,但长远看,它严重破坏了产权保护的契约基础,让民营企业家对与权力合作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这正是 2026 年我们看到民间投资意愿彻底冰冻的深层原因之一。
更可怕的是,正如 Lardy 所观察到的,到了 2018 年左右,这种“混改”甚至出现了一种逆向的趋势:不再是民资入股国企,而是国企趁着民企资金链断裂之际,大举收购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在公权力缺乏约束的背景下,所谓的“混改”,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关门打狗”的陷阱。民营企业家们带着技术和资金进去,最终却发现自己成了任人摆布的附庸。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无法激活国企,反而会把最具活力的民营资本拖入低效的泥潭。
此外,Lardy 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国企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即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法定地位的确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会是代表股东利益的最高决策机构,它负责挑选管理层、制定战略、考核绩效。这套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建立在清晰的委托 - 代理关系之上,目标函数非常单一且明确——就是利润最大化。但是,当党委会的前置研究成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当“党管干部”原则覆盖了企业的管理层任命时,这家企业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主体,而变成了一个执行政治意志的半行政机构。这种变化意味着,企业的决策不再仅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要考虑政治站位、社会稳定、宏观调控等各种非经济目标。当一个机构同时追求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时,它注定什么都做不好。对于国企管理者来说,只要政治上不出错,经济效益差一点是无所谓的;反之,如果为了追求效益而触犯了政治原则,那乌纱帽就不保了。这种激励机制的扭曲,直接导致了国企行为的僵化和保守。它们宁愿守着垄断资源过日子,也不愿意去市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
2026 年 1 月 31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