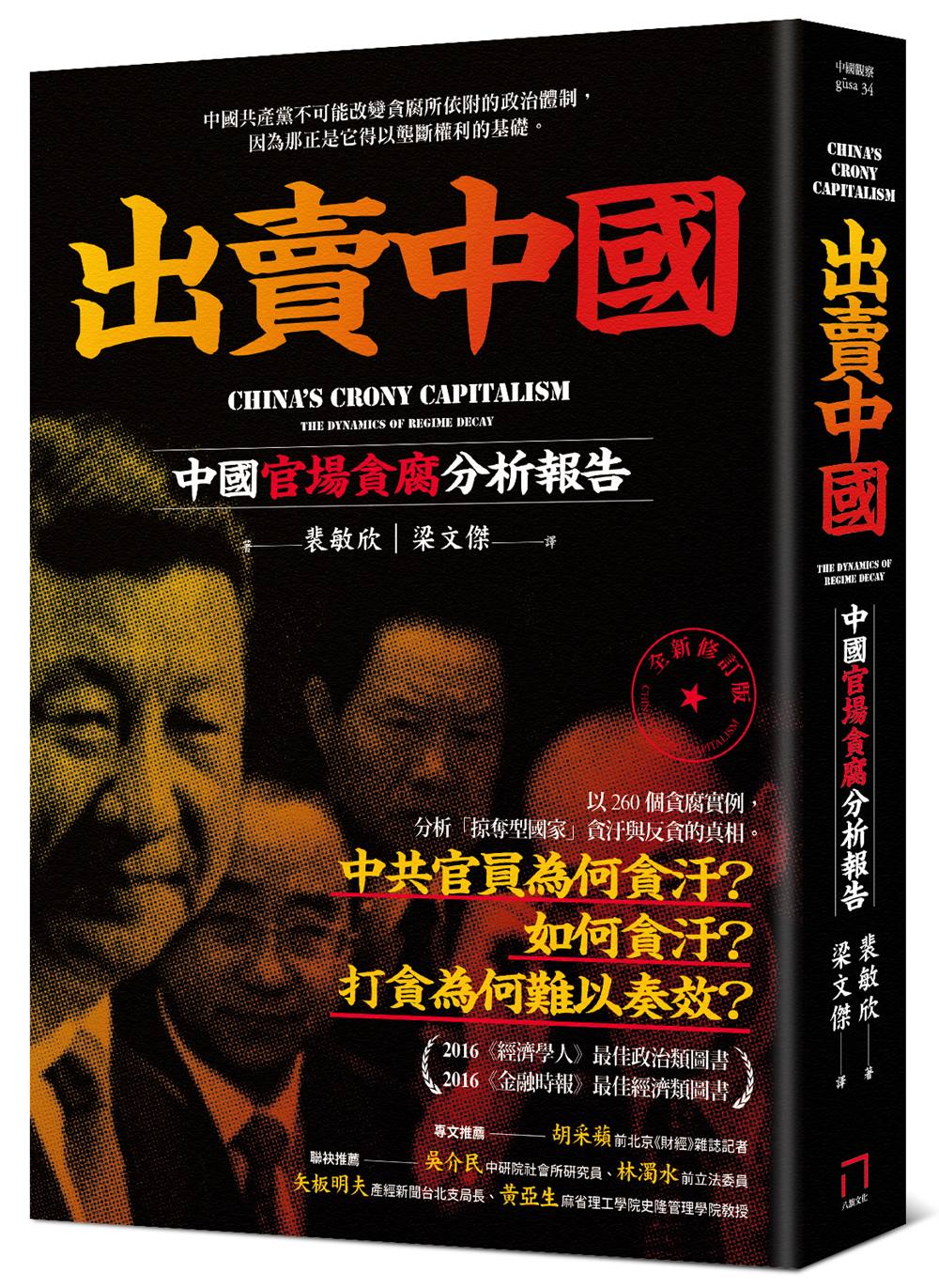
张东云:反腐亡党亡国,不反腐也亡党亡国(中)
在一般的解读中,列宁式政党通常被视为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纪律、强调意识形态忠诚的体系。然而,裴敏欣在书中通过对数百个案例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如下的事实:这个庞大的党国机器,在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下,其内部的组织机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癌变。官僚体系内部的选拔与晋升,不再主要遵循韦伯式的理性原则或官方宣称的“德才兼备”标准,而是退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职像商品一样被明码标价,政治权力被货币化,上下级关系异化为一种基于金钱交易的“纵向勾结”,而以革命起家的共产党也转型成了一个通过贩卖国家权力来分赃的利益集团。
我们还是要从刚才已经提到过的 1984 年中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说起,将人事管理权限从“下管两级”下放为“下管一级”,赋予了地方党委书记——也就是所谓的“一把手”——对其直接下属近乎垄断的任免权。这种权力的下放,在缺乏监督的真空中,使得“一把手”在辖区内拥有了封建领主般的绝对权威。于是,县委书记成为了最大的“卖方”,而渴望晋升的下属则成为了“买方”。这种“纵向勾结”的市场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核心还是在于“官位”本身所附带的巨大经济价值,或者说能够合法抢劫所附带的经济价值,所以贿赂就不再是单纯的贿赂,我们可以说贿赂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基于预期收益率(ROI)的风险投资。
在书中,裴敏欣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了官位价格的通货膨胀现象:从 1990 年代初的几千、几万元,飙升至 2000 年代后的数十万乃至上千万元。这种价格的飙升可以说反映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价值的提升。一个县交通局长的职位之所以能卖出天价,是因为买官者心里清楚,一旦坐上这个位置,他就可以通过发包工程、收取回扣等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回“购官成本”并实现巨额盈利。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官员的合法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高昂的“买官费”。那么钱从哪里来?裴敏欣通过对大量判决书的分析发现,买官者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挪用公款,即直接窃取其管辖单位的公共资金作为“政治投资”;二是贪污受贿的积蓄,即用过去的非法所得购买未来的非法所得;三是,也是最为关键的,来自私营企业家的“赞助”或“贷款”。这种“官商融资”模式构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运作当中的循环:企业家为官员提供买官资金,官员上位后则利用手中的审批权、执法权,在土地出让、项目审批、司法案件中为企业家提供超额回报。这种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权钱交易,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命运共同体”。对于企业家而言,资助官员买官是一种高风险但高回报的风险投资;对于官员而言,接受企业家的资金则意味着在政治上被“俘获”。这种融资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在反腐风暴中,往往一个官员落马会牵出一串富豪,或者一个富豪被抓会引发官场地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权力市场已经与地下金融市场、灰色商业市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黑金网络。
在这一章节的分析中,裴敏欣还特别强调了“一把手”如何通过制造“需求”来活跃这个市场。为了最大化卖官收入,贪腐的党委书记们往往会频繁地进行干部调整,人为制造职位空缺,或者通过“轮岗”等名义将肥缺拿出来重新拍卖。这种为了卖官而卖官的折腾,导致了地方行政体系的极度不稳定和短期行为。官员们刚刚熟悉业务,就因为没钱“续费”或者因为领导想卖给别人而被调离;新上任的官员为了尽快还清买官的债务并赚取利润,必然会在任期内变本加厉地进行掠夺。这种“短期化”的掠夺行为,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它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导致了对环境资源的竭泽而渔,导致了对企业和民众的苛捐杂税。正如裴敏欣所言,当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干部队伍——本身成为交易的商品时,这个国家就已经丧失了追求长远发展目标的能力,它剩下的只有对眼前利益的疯狂追逐。
然而,裴敏欣在 2025 年的论文中指出,习近平政权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山头主义”和“团团伙伙”对中央集权的致命威胁。因此,通过三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中共大幅扩张了“违反政治纪律”和“违反组织纪律”的定义。诸如“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结交政治骗子”(2018 年及 2023 年修订版新增)等条款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对《出卖中国》中所描述的“纵向勾结”行为进行的政治定性。这表明,当下的中共试图用泛政治化的罪名来打击经济性质的官位买卖,将原本的“贪腐问题”上升为“政治忠诚问题”。这种从经济逻辑向政治逻辑的转向,并没有消灭“官位市场”,反而导致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剧增和交易标的的异化。在《出卖中国》中,裴敏欣分析了马德案等典型案例,指出买官者通过贿赂获得职位,目的是为了后续的经济掠夺。而在《从整肃到控制》的分析框架下,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交易动机:寻求政治庇护。裴敏欣在论文中通过对 2023 至 2024 年间大量官员处分案例的统计发现,约有 7% 至 8% 的中层官员被指控“结交政治骗子”或“搞政治攀附”。这揭示了一个荒诞而残酷的现实:在反腐高压下,地方官员为了在官僚阶梯上生存,或者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清洗中获得豁免,由于缺乏正规的晋升渠道和安全感,不得不病急乱投医,试图通过贿赂所谓的“背景人士”(往往是政治骗子)来与上层权力建立联系。这说明,“纵向勾结”的需求不仅没有因为高压反腐而消失,反而因为官员普遍的不安全感而变得更加强烈。现在的“买官”,更多时候是在“买命”——购买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基于恐惧的交易,使得官场内部的依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且具有黑社会性质。
更为关键的是,裴敏欣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中共如何利用程序性工具来瓦解这种勾结网络,其中最核心的武器便是“对抗组织审查”。在《出卖中国》中,裴敏欣强调了腐败官员之间通过“攻守同盟”来掩盖罪行,而在 2025 年的论文中,他指出“对抗组织审查”已经成为了纪委清洗官员的头号罪名。根据裴敏欣对 2023-2024 年样本数据的分析,高达 30% 的高级官员和 77% 的中层官员在落马时都被指控犯有此条罪行。这一数据的极高比例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官僚体系内部的“勾结”依然根深蒂固,面对调查,官员们的第一反应依然是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伪造证据,这正是裴敏欣在书中描述的“精英勾结”的典型特征;第二,中共高层已经将打破这种勾结作为反腐的首要战术目标。通过将“对抗组织审查”列为严重的政治违纪,党机器获得了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口袋罪”,任何试图自我辩护或保护同僚的行为,都可以被定性为对党不忠。这实际上是要求官员在面对组织时必须彻底透明,交出所有隐私和尊严,以此来换取从轻发落的可能。这种极端的控制手段,旨在彻底粉碎官员之间的横向和纵向信任,将每一个官员都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使其只能依附于最高领袖。

然而,这种依靠恐怖和纪律泛化维持的“控制”,最终导致了官场生态的全面恶化和“逆向淘汰”机制的升级。在《出卖中国》中,裴敏欣指出“买官卖官”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只有贪婪者才能上位。而在《从整肃到控制》中,我们看到了这种逆向淘汰的 2.0 版本:由于“妄议中央”、“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互联网资讯”等行为都可能导致政治清洗(如论文指出,2023-2024 年样本中有官员因阅读禁书被处分),官员们变得极度伪善和避险。那些能够在这个新市场中生存下来的,不再仅仅是有钱买官的人,而是那些擅长表演政治忠诚、能够精准揣摩上意、并且随时准备出卖同僚以求自保的“两面人”。这种政治生态的恶化,比单纯的金钱腐败更为致命,因为它切断了体制内部的信息反馈机制,使得决策层听不到任何真实的声音。习近平试图用列宁主义的纪律来替代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试图用“控制”来取代“收买”,结果却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为了控制官员,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纪律红线和政治罪名;而红线越多,官员的不安全感越强,就越需要通过结党营私和政治攀附来寻求保护。这种恶性循环不仅无法根除腐败,反而制造了一个人人自危、效能低下且充满猜忌的“僵尸化”官僚体系。虽然“买官卖官”的形式可能因为高压打击而变得隐蔽,但其内在的驱动力——即在缺乏法治和民主监督的体制内,官员必须寻找靠山以获取资源和安全——从未改变。这表明,只要权力的来源不是基于民众的授权,而是基于上级的任命,那么无论如何修补纪律条文,无论抓捕多少“大老虎”,权力的私有化和权钱交易就会永远伴随着这个体制。
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运作机理,就会发现“买官卖官”虽然构建了腐败的组织基础(即“谁来掠夺”),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富生成的源头,而只是权力分配的机制。真正让这个庞大的掠夺型机器产生惊人经济效益的,是官员与商人之间通过勾结所实施的国有资产非法转移。裴敏欣在《出卖中国》中用大量篇幅解剖了这一过程,他将这种行为精确地定义为“精英勾结下的资产掠夺”(Collusive Asset Stripping)。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受贿,而是一种复杂的金融与法律工程,其核心在于利用中国转型期特有的“双轨制”缝隙——即行政指令控制下的低价资产与市场经济下的高价变现之间的巨大价差——进行系统性的套利。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行贿者,更是官员们不可或缺的“白手套”。由于党纪国法(尽管执行并不严厉)在形式上禁止官员直接经商或持有股份,官员们必须通过代理人来完成从公共权力到私人财富的惊险一跃。这种合作模式在土地出让、矿产资源开发以及国有企业改制这三大领域表现得尤为猖獗,它们构成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三大“提款机”。
首先,土地市场无疑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现场,也是官商勾结最为惨烈、最为暴利的领域。裴敏欣在书中通过对大量司法判决书的分析,揭示了土地腐败的内在逻辑:国家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征收与出让),而地方官员掌握了绝对的审批权。在 2004 年“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全面实施之前,大量的土地是通过不透明的“协议出让”方式转手的。这种制度设计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天然的温床。一位拥有签字权的市委书记或国土局长,可以以极低的“行政价格”将一块商业用地批给与其结盟的开发商,而开发商转手就能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市场价格进行开发或倒卖。即便在“招拍挂”制度实施之后,这种掠夺也没有停止,只是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技术化。裴敏欣细致地列举了诸如“量身定做”标书条件、操纵容积率修改、甚至在拍卖现场进行围标等手段。例如,在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中,我们看到了陈良宇及其亲信如何通过复杂的金融运作,将巨额社保资金违规贷给商人张荣坤,帮助其在上海高速公路和房地产市场大肆并购。这并非孤例,而是普遍存在的模式:权力和资本结盟,利用不受监管的公共资金(如社保基金、银行信贷)作为杠杆,撬动巨额的国有土地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增值收益(Land Increment Value),并没有转化为公共福利,而是流进了权贵家族和依附于他们的地产大亨的腰包。这种掠夺的残酷性还在于,它往往建立在对底层民众财产权的粗暴践踏之上——大规模的暴力拆迁和低价征地,正是这根贪婪链条的起点。
其次,自然资源(特别是煤炭、有色金属和石油)领域的官商勾结,展示了另一种形式的资产流失。如果说土地财富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中心,那么资源型腐败则深刻地腐蚀了中国内陆资源丰富的省份,如山西、内蒙古、云南和黑龙江。裴敏欣在书中深入剖析了“采矿权”审批背后的黑箱操作。根据中国法律,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开采权需要政府审批。这种审批权在实践中变成了一种可以私相授受的特权。我们看到了如刘汉这样的“黑金帝国”是如何在四川崛起的:通过结交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法王周永康家族(特别是其子周滨),刘汉可以轻易获得他人无法企及的优质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清除竞争对手。在山西的煤炭领域,更是出现了所谓“官煤勾结”的生态,地方官员不仅收受煤老板的巨额贿赂,更通过“干股”的形式直接参与分红。所谓“干股”,即官员不出资,仅凭权力入股,这是一种将公权力直接资本化的极端形式。这种勾结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了最大化短期利润,官商联盟往往无视安全生产法规和环境保护标准,导致矿难频发、环境毁灭。这种掠夺甚至波及到了央企层面,在中石油腐败窝案中,我们看到了国有资产是如何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被输送给周永康家族代理人的私营企业。这种“寄生”关系表明,即便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巨型央企,也未能幸免于权贵集团的瓜分。
第三个,也是最具技术含量和隐蔽性的掠夺领域,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与重组。1990 年代末期,中国在“抓大放小”的政策口号下开启了大规模的国企产权改革。这本应是一场旨在提升效率的市场化改革,但在缺乏法治监管和民主监督的真空中,它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欢。以“管理层收购”为例,在书中提及的许多案例中,国企管理层(往往本身就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利用手中的信息优势和控制权,故意隐瞒企业资产、虚构债务、制造亏损假象,以此压低企业评估价值,然后利用挪用的公款或银行贷款,以极低的价格将企业“买”下来,摇身一变成为私营企业主。书中详细剖析了顾雏军案、健力宝案等经典案例,揭示了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更为恶劣的是“左手倒右手”的操作:国企高管在体外设立由亲属控制的私营公司,然后将国企的高利润业务、优质资产或核心技术转移到这家私营公司,而将债务、劣质资产和冗员留在国企。这种掏空行为,使得大量国企在账面上连年亏损,需要国家财政不断输血,而依附于其上的寄生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反而为权贵集团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掠夺通道。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被迫下岗(被买断工龄),他们承担了改革的所有代价,而改革的红利却被一小撮不仅没有任何创业贡献、反而通过侵吞公产致富的“红色资本家”所独占。
此外,在分析这些手段时,裴敏欣还特别强调了“家族式腐败”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在中国这种缺乏法治契约精神和普遍信任的社会环境中,非法交易面临着巨大的违约风险和检举风险。如何确保“白手套”在发财后不背叛?如何确保赃款的安全?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网络成为了解决这一信任难题的替代机制。因此,我们看到了“全家腐”的普遍模式:官员在台前掌握权力,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在幕后经商,利用官员的影响力变现。书中提到的周永康家族、令计划家族、薄熙来家族,无一不是这种“家国一体”掠夺模式的典型代表。官员的子女(“官二代”或“太子党”)利用父辈的政治资源,在金融、私募股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不需要像传统行贿者那样提着现金去收买官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力的延伸。这种基于血缘的利益输送,比直接的权钱交易更隐蔽、更高效,也更难以查处。它导致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固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袭的权贵阶层,以及一个个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封建化统治集团。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