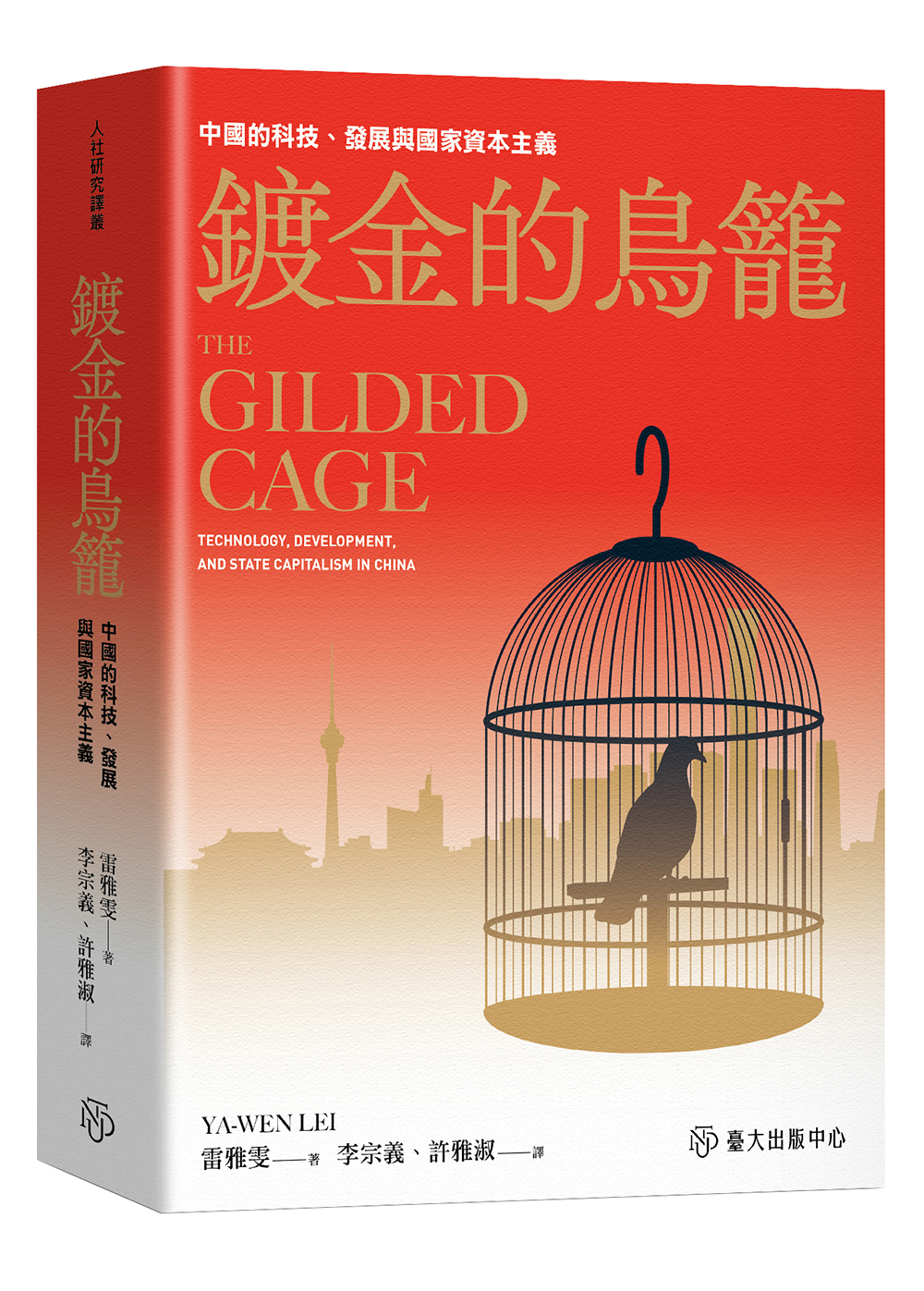
镜空:“中国式现代化”还是“通往奴役之路”?评雷雅雯“The Gilded C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上)
雷雅雯这本书,取名叫《镀金的鸟笼》(The Gilded Cage),很见巧思。这让我想起早年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鸟笼经济”之说。那时候,“鸟”是市场经济,要放活;“笼子”是国家计划,要管住。鸟要飞,但不能飞出笼子去。这个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当年中共摸着石头过河,既要搞活又要可控的矛盾心态。
几十年光景过去,雷雅雯这本书告诉我们,鸟和笼子的名堂都变了。今天的“鸟”是谁?“笼子”又是什么?这个笼子,不再是当年那个简陋的铁丝笼,而是“镀金”的,金光闪闪,看上去华丽、坚固,甚至让人羡慕。但鸟终究是鸟,笼子终究是笼子。这金光闪闪的背后,笼中人的真实处境又如何?雷雅雯以一位社会学家的细腻观察和多年的田野功夫,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纠缠的复杂图景。这幅图景,与其说是鸟笼,我看倒不如说,更像福柯笔下那座“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种更精致、更深入骨髓的规训体制。身处其中的人,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但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监视的存在,于是只好自我约束,按照规训者的意图行事。
这本书的核心关切,追根究底可以归结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当下这套由国家强力主导的“技术 - 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techno-state capitalism),是否真的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且可持续的康庄大道?抑或,这种模式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其“镀金”的表象之下,是社会活力的窒息和个体权利的全面让渡,最终将导致整个体系因僵化而变得脆弱?
本文第一部分,先看看这个新“笼子”是怎么来的,探讨一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技术转向”;第二部分,讲讲“鸟”的更替,看看这场由国家主导的“创造性毁灭”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三部分,分析一下“新鸟”,也就是平台科技巨头的崛起,以及它们与“笼子”之间那种既共生又紧张的关系;第四部分,也是最重要的,要看看形形色色的“笼中人”——无论是被淘汰的“旧鸟”,还是被圈养的“新鸟”——他们的真实处境和喜怒哀乐。
一、
凡事要有个由来。雷雅雯这本《镀金的鸟笼》,讲的是当下中国的故事,但要把这个故事说清楚,还得从“土地财政”看起。这四个字,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差不多就是中国城市化这部大戏的“戏眼”。上世纪九十年代搞分税制改革,地方上钱袋子紧了,事权却没少,怎么办?眼睛只好盯上了脚下的土地。于是,“一手征地、一手卖地”的模式应运而生。这套办法,好不好?当然好。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基础建设一日千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靠的就是这笔从土地里“生”出来的钱。这套办法,有没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
雷雅雯这本书的观察,恰恰是从这个我们熟悉的逻辑走到瓶颈处开始的。她敏锐地发现,大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原先那套玩法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玩不转了。原因很简单: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过去靠“三来一补”就能发财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地方主政者们普遍陷入了一种“增长焦虑”。旧的增长引擎眼看要熄火,新的引擎又在哪里?
于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应运而生——“腾笼换鸟”。这个词很生动。“笼子”是什么?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政策空间。“鸟”又是什么?是那些占着“笼子”的企业和产业。要把“旧鸟”——也就是那些劳动密集、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请出去,把“新鸟”——高科技、高附加值、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引进来。雷雅雯在书中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中国向“技术 - 发展型政体”(techno-developmental regime)的转向。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场产业升级,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模式变革。地方政府的角色,从过去那个提供土地、修桥铺路的“开发区主任”,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精挑细选的“风险投资家”。增长的赌注,不再押在“人海战术”和“土地扩张”上,而是押在了“技术红利”和“工程师红利”上。这个“镀金”的新笼子,最初就是这么来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增长焦虑,给自己找到的新出路。
问题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一个地方官,凭什么就能分得清谁是“好鸟”,谁是“坏鸟”?凭感觉?拍脑袋?那和大跃进又有什么分别?雷雅雯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为我们细致地描绘了这套“鸟/笼逻辑”(bird/cage logic)是如何具体运作的。答案是,靠一套全新的、号称“科学”的“增长标尺”,也就是雷雅雯笔下的“工具性装置”(instrumental apparatus)。
这个“装置”说白了,就是把过去那种模糊的、凭经验的招商引资,变成了一套精密的、量化的绩效评估体系。这套体系无所不包,上至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中至筛选一个投资项目,下至评判一个具体的人才。雷雅雯在书里给我们展示了广州某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洋洋洒灑,从 GDP 增速、财政收入,到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比、R&D 经费支出占比,几十项指标,每一项都有明确的分值和正负向。一个地区的工作好不好,不再是“面貌一新”这种模糊的文学描述,而是看这些 KPIs(关键绩效指标)的得分。
企业也一样。你想被当成“好鸟”请进笼子里来,享受土地、税收、信贷上的种种优惠?那得先填表,接受“科学”的评定。雷雅雯展示的《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表》就是这么个东西。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发组织管理水平……每一项都量化打分,最后得出一个总分。分数够了,你就是“高新企业”,是座上宾;分数不够,对不起,你就是“过时产能”,是“旧鸟”,得赶紧腾地方。
最有意思的是,连人也开始被这套“标尺”来衡量。我们过去讲户籍制度,是把人简单粗暴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现在这套办法显得“科学”多了。雷雅雯详细分析了深圳的“积分入户”制度。学历、技能、纳税额、有无房产、甚至献血和做义工,统统折算成积分。分数高的,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市民”,享受这里的公共服务。雷雅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人力资本”的筛选,它系统性地偏爱那些“高学历、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将广大的“低技能”劳动者排斥在外。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哈耶克对“惟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深刻批判。当人们过于迷信所谓“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时,当复杂的社会现象被强行简化为可以计算和规划的指标时,其结果往往不是更科学,而是更武断,是“致命的自负”。地方政府试图扮演全知全能的“规划者”,用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的指标体系来甄别“好鸟”与“坏鸟”,这本身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市场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允许无数匿名的个人去试错、去探索,从而发现那些任何“规划者”事先都无法预见的价值。马化腾当年搞 OICQ 的时候,哪家政府的“评价体系”能算出来他会成为一只价值万亿的“好鸟”?
这套“工具性装置”一旦建立起来,就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应,或者说,扭曲效应。对地方官员来说,工作的目标不再是真正地服务地方经济,而是做出漂亮的“数据”,在考核评比中胜出。对企业来说,经营的目标不再是满足消费者需求、创造价值,而是在各项评估中“刷分”,以获取政府补贴和政策倾斜。于是,我们看到各种荒诞的现象:企业为了凑够专利数量而去申请大量毫无价值的“垃圾专利”;为了达到研发投入的指标而虚报开支。每个人都围绕着这套“标尺”在行动,都在“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得分,但整个体系的真实效率和创新活力,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悄悄侵蚀了。雷雅雯称之为“超工具理性”(hyper-instrumentally rational),我看,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唯指标论”,形式主义。
这场“技术转向”最大的新特征,是国家权力与现代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靠的是算盘、电话和文件,那么今天的“技术 - 国家资本主义”靠的则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雷雅雯在书中提到的“数字驾驶舱”(digital cockpits),就是这个新体制的绝佳写照。地方主政者们坐在巨大的电子屏幕前,看着上面实时跳动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仿佛运筹帷幄的指挥官。城市被视为一个可以被数据化、可以被“优化”的复杂系统。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插上了技术的翅串膀,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精准时,它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但实际情况呢?当政府手握所有数据,并试图用一套统一的算法来配置所有资源时,市场自发调节的功能还剩下多少?当一个企业能不能拿到土地、贷款,不再取决于它的产品有没有市场,而是取决于它在政府的评估系统里得分高不高时,企业家精神还有多少生存空间?
这套被技术高度赋能的“笼子”,看似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服务市场这只“鸟”,但它自身的运行逻辑,却越来越像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强化的权力系统。它用“科学”和“发展”的名义,将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简化为冰冷的指标;它用强大的数据和算力,将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变成其精算和管控的对象。这个笼子,远比先生当年那个简陋的“鸟笼”要复杂、要精致,也因此更加坚固、更难逃脱。它外表镀着一层耀眼的技术和效率,但其内核,仍然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和主导。这与其说是习近平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如说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二、
经济学里有个词,叫“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是熊彼特提出来的。说的是市场经济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出来,就会把旧的给淘汰掉。这个过程看着残酷,却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像汽车出来了,马车夫就得失业;数码相机普及了,胶卷厂就得关门。这个道理不难懂。
不过,读雷雅雯这本书,我发现中国的这场“鸟”之更替,味道不太一样。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灭”,动力来自市场,是企业家和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是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场由国家权力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雷雅雯在书里专辟一章,讲“过时资本与劳工”(Obsolete Capital and Labor)的命运,读来让人心情沉重。
故事的主角,是那些曾经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曾几何时,它们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是解决就业、创造税收的“香饽饽”。雷雅雯的田野调查集中在珠三角,那里的情况我们都熟悉。当年的中共乡镇干部,为了招商引资,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只要你肯来投资,土地、税收、劳工,一切都好商量。正是这种“地方法团主义”,加上无数农民工的辛勤汗水,才有了后来几十年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
然而,风向说变就变。还是那个“腾笼换鸟”的逻辑。当地方政府的“增长标尺”从 GDP 转向“高科技”和“创新”时,这些昨日的功臣,一夜之间就成了“落后产能”,成了“笼子”里必须被清理出去的“旧鸟”。雷雅雯的访谈里,企业家们充满了困惑与愤懑。他们发现,原本笑脸相迎的官员,变得横眉冷对;原本行得通的做法,突然就“违法违规”了。
怎么个清理法?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行政手段。雷雅雯记录了地方政府的“组合拳”:环保、消防、安监、劳工等部门轮番上阵,以“执法”的名义进行高强度的检查。今天说你排污不达标,明天说你消防有隐患,后天又说你用工不规范。标准呢?说变就变,而且越来越严。一位企业主抱怨道:“他们早上发一个命令,晚上就能废掉它。”另一位则说得更白:“政府就是不想让你活了。”罚款、停产整顿、甚至直接查封关停。这些曾经被容忍甚至鼓励的“灰色地带”,如今都成了套在民营企业头上的紧箍咒。
这背后是什么道理?真的只是为了“绿水青山”或者“安全生产”吗?雷雅雯的分析指出了更深层的原因。这些严苛的执法运动,往往与地方政府清理土地、为“新鸟”(高科技产业和房地产)腾挪发展空间的意图紧密相连。一家“旧鸟”工厂被关停,它占用的那块宝贵的工业用地就可以被“盘活”,重新招拍挂,引进更“高端”的项目,既完成了产业升级的 KPI,又为地方财政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执法行动常常是“运动式”的,充满了选择性和随意性。一位官员甚至向雷雅雯坦言,这就是“杀鸡儆猴”,就是要制造一种高压态,迫使这些“低端”企业自己“知难而退”。
这个过程,深刻地暴露了中国民营企业产权的根本脆弱性。我们讲市场经济,基础是产权。你的财产是你的,受法律保护,不能被随意侵犯。可是在“腾笼换鸟”的运动里,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家的财产权,包括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其价值的生杀予夺,并不由市场决定,而是取决于政府的一纸文件、一场运动。当你是“好鸟”时,你的产权是安全的;当政策风向一变,你成了“坏鸟”,你的产权就岌岌可危。
雷雅雯访谈中的企业家们那种普遍的焦虑和无力感,根源就在于此。他们面对的,不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可预期的风险,而是来自政府行为的、完全不可预测的“政策风险”。一位企业家说得好:“我们不怕市场竞争,但政府的干预正在杀死我们,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预期他们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在这样一个“规则可以随时改变”的环境里,企业家怎么可能做长期投资?怎么敢投入巨资搞研发创新?他们最理性的选择,反而是“捞一把就走”,搞短期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腾笼换鸟”运动,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但它采用的手段,却恰恰在破坏创新所必需的最根本的制度基础——稳定的产权预期和法治环境。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比“过时资本”的命运更令人揪心的,是“过时劳工”的处境。如果说企业家们还尚有资本可以转移,尚有发声的渠道,那么千千万万在这些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命运就更加被动和无声。
雷雅雯准确地捕捉到了官方话语体系里一个冰冷而残酷的词——“低端人口”。这个词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更精致也更残酷的社会排斥机制的形成。过去我们讲城乡二元结构,那道鸿沟主要基于户籍,是身份上的。现在,一道新的鸿沟出现了,它的标准是“人力资本”,是“对技术发展的贡献度”。
谁是“低端人口”?在“腾笼换鸟”的逻辑里,就是在那些“低端”产业里从事“低端”劳动的工人。雷雅雯书中引述一位地方官员的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研究发现,两个低端人口会带来一个低端服务提供者……产业转移最终将有助于驱逐低素质人口。”话虽刺耳,却道出了这套政策背后的冷酷算计。城市需要的是“人才”,是能够为“高精尖”产业做出贡献的“高端人口”。至于那些曾经为城市建设流血流汗的农民工,一旦他们所在的产业被判定为“落后”,他们也就成了城市想要摆脱的“负担”。
这种排斥是如何实现的?雷雅雯的分析直指要害——通过公共服务的选择性供给。教育,就是最核心的一环。农民工的孩子想在城市里上学?可以,但要通过严格的积分制度来筛选。这套积分制度,说白了,就是为父母的“价值”打分。高学历、高技能、有房产、纳税多的“高端人才”,他们的孩子可以轻松进入优质的公立学校;而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低端人口”,他们的孩子则很可能被拒之门外,要么回老家做留守儿童,要么只能去上收费高昂、质量堪忧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雷雅雯在调研中也反复听到类似的故事。一位在东莞打工的母亲,为了让孩子能上公立学校,想尽办法考各种职业证书来“加分”。她说:“我知道那些证书没什么用,但为了孩子,没办法。”这种以“贡献”为名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差别配置的做法,不仅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更是在代际间固化了这种不平等。它斩断了底层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形成了一个新的“身份”壁垒。这不再是简单的城乡之别,而是在城市内部,用教育、住房等公共资源,划出了一道看不见的、却难以逾越的鸿沟。一边是生活在配套完善的社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科技精英”;另一边则是居住在城中村、子女入学无门的“低端劳工”。
这种做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和伦理危机。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代价是将一部分人定义为“低端”而加以排斥和牺牲,那么这种发展的正当性何在?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又怎能心安理得地将它的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为据来分配公共资源?这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底色的治理逻辑,与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包容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它或许能在短期内提升城市的“品质”和“竞争力”,但长期来看,必将撕裂社会,埋下巨大的冲突隐患。
总而言之,雷雅雯对“鸟”之更替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创造性毁灭”的另一面。它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市场过程,而是一场由国家权力精心策划和强力推动的社会工程。在这场工程中,效率和增长的宏大叙事压倒了一切,而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则被轻易地牺牲。资本的产权是不安全的,劳动者的尊严是可疑的。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企业家失去了安全感和长期预期,劳动者失去了希望和向上流动的阶梯,而整个社会,则可能在“镀金”的表象下,逐渐失去其内在的活力和凝聚力。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