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虞夫专辑】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二)
(二)萧山遣送站
5、脱逃机会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期限,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将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
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如果爬上墙,跳出去,那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
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许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像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被抓被判本身就是共产党在为我们做广告。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躯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那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
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这个政权“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
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又怕自己某天抗不住诱惑,干脆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6、监视居住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彘(猪)还不如”。时逢炎夏酷暑,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依山而建的废弃看守所笼板已经被白蚁蛀空朽烂了,破败的洞窟下塞满历年关押者丢弃的垃圾。霉菌大举肆虐,皮肤、阴囊严重湿疹,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
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甚至许多无辜者——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坚强的意志在支撑着我,我明白能使自己增强免疫力的只有良好的心态了,我顽强地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放开嗓子高唱歌曲,这一招还真行,几嗓子下来,神清气爽。遣送站有一个姓陈的科长进来检查,揶揄我说:“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999 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一点也没有寂寞的感觉,还常常涌起缕缕的灵感,写下许多首诗,让隔壁放出去的人带进纸笔来,抄给他们。底稿我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关押在杭州看守所被武警“抄笼子”抄走了。
八月初,姓陈的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所在地的)公安,(他们)怎么还不来带你走?”这一次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也许是度假地的优美风情与眼前现实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震撼,使他的良心有所触动吧。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自己也在墙上刻下一个一个的“正”字,每字五天,顺便推算日期,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三)转移
1、特警队里
8 月 13 日,郑刚终于来了。遣送站的人进来通知我带好东西,走。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神情恍惚,浑身虚脱,院子里的阳光使我一阵眩晕睁不开眼,高一脚低一脚随那人到大楼前的警车旁,郑刚一声不吭,脸上挂着讪讪的笑,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我们彼此保持沉默。
上了车走了。警车过了江,向着杭城北面驶去,在一条冷僻的小巷里停下,因为离开萧山时,监舍里的人把我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去了,一旦关在这里面,生活会非常不便,于是我摸出口袋里的几十元钱要郑刚为我买一些诸如牙膏、牙刷之类的物品,郑刚拒绝了,说:“你上去,他们会给你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郑刚。后来,我入狱后他多次去我爱人单位骚扰、威胁、恐吓我爱人,没收了海外朋友补助我家用的款项,并到处散布侮辱我爱人的流言,为此,毛庆祥爱人胡晓玲指责了他并要他出示证据,他卑怯地抵赖了,作为一名政治特务,他在对民主党和法轮功的镇压中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这是后话了。
我被带到杭州市下城区公安特警队队部,这里的四楼用铁栏杆围起来,作为关押经济诈骗犯“监视居住”的地方。靠东两间再用栏杆隔离,一间是警察值班室,一间是“禁闭室”——关押我的监室。在里面已经关着一个叫徐百加的朝晖街道河西村委会干部,他兼有监视我的责任,但他人很不错,也很信任我。当我习惯性地在墙壁上找“文化”,看到祝正明刻写的“专制必败,民主必胜”的字样,问他原先关的人的情况时,他简单地告诉我祝已经由原来的单位取保候审了,并非常紧张地告诫我,千万别让警察知道他对我说的事。
正是凑巧,我关押的两个地方都是祝正明关过的,我从他留下的字迹看到了他的决心和勇气,我从心里为他祈祷,愿他自由。祝是一个少年神童,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熟稔地掌握精博的民主理论,宽容大度身体力行,待人也极为厚道。
1998 年,大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是杭州首议、各地响应、势成燎原,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祝氏的淡泊心态。当时,祝将新党起名为“中国民主党”并在后面接上“浙江筹委会”字样,意在“浙江搭台,大家唱戏”,摒弃了以往屡见不鲜的“占山为王”做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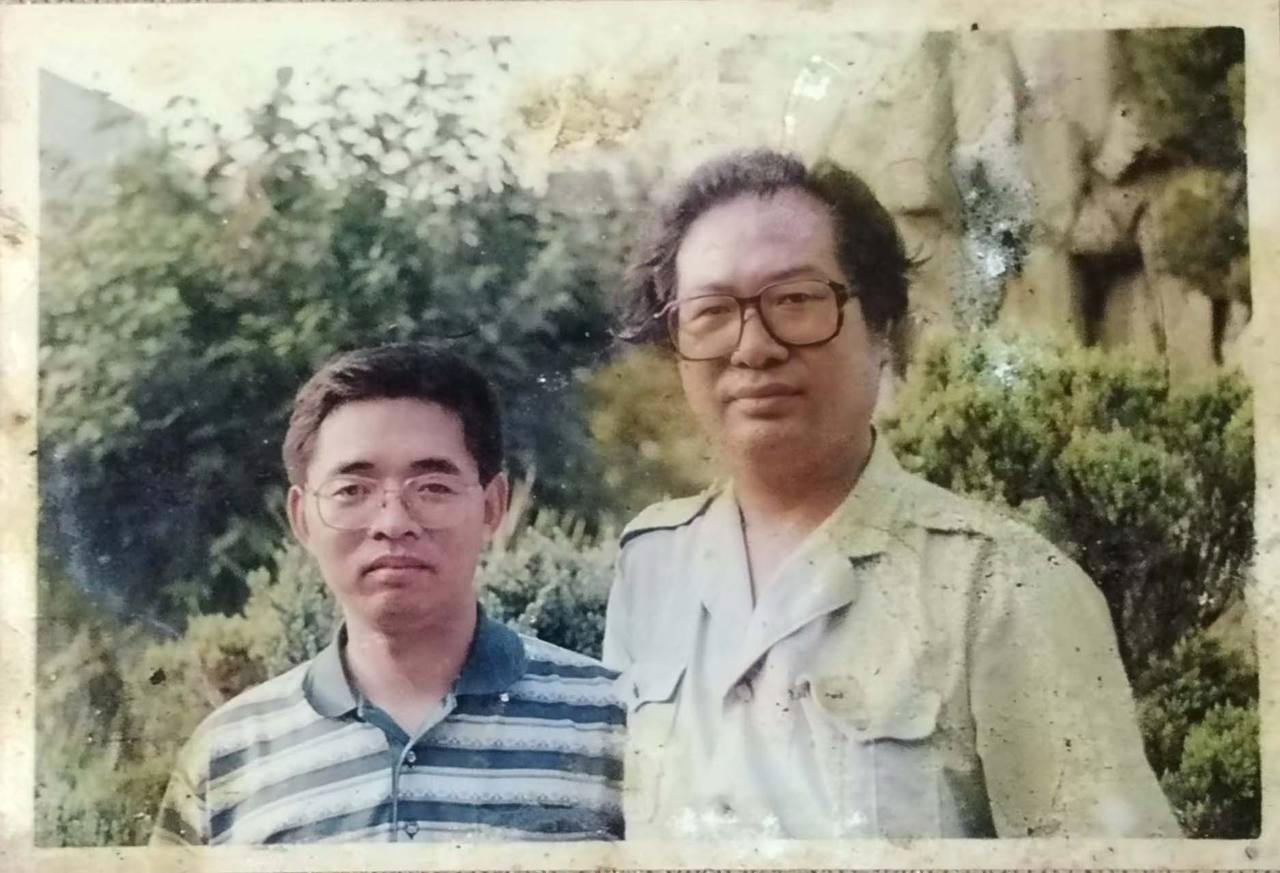
但是,祝并不是一个“玩政治”的人,记得当年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去浙江民政厅为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有关方面官僚颟顸地说要“研究研究”拖延时日,我决心燃一把促进之火,拿起《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到街路上去散发,被抓进公安局,祝正明竟极其痛苦和内疚,自责不已。如此性情中人与我颇为相似,优柔如我等者竟试水政治,岂有不遭灭顶之理。但是,倘若我们对如此并不美好的现实视若无睹,似乎又无法承受来自良心的压力。我很关切祝,早过了婚嫁年龄的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他美丽贤淑的女朋友很可能因为祝的不幸入狱而终身无所托付。想到这些,我对自己将面对的苦难看得更淡然了。
2、满足愿望
8 月 30 日,预审处来了几个人提审,有个叫陈伟星的问我,“你认不认识许光?”我说不认识。他狡黠地一笑,似乎我在骗他。(事后我才想起,他指的是徐光,只是他在杭州话里夹了普通话,让我听糊涂了。杭州话“徐”的发音是 QU。)然后,陈伟星说:“关于你的案子,有人说你已经淡出民运,可是我春节在火车站值班时,从一个民工身上搜出了你的中国民主党名片,我问那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人说是你在湖滨亲自给他的,我问那人你的长相,那人说的很像,所以,我认为你没有淡出。”当时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心里暗暗好笑,他以为他是谁,可以轻轻松松地为中国政府背上沉重的人权包袱。其实,我从来没去湖滨发名片,我的名片都是王荣清去发的,那时他说他的名片发完了,拿我的用用。可是我面对着狂妄的陈,不想辩白,以免助长了他的邪气,不知以后到了民主社会,此人是否也会有这副神气来承担自己今日的作为。看到我一脸的不屑,旁边那个姓许的咬着牙(也许他生相如此)冷冷地说:“朱虞夫,这次我们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坐牢。”我微微一笑说:“谢谢,我愿意。”陈伟星怏怏地说:“好了,开着空调,不要浪费共产党的钱了,到此结束吧。”我马上说:“共产党哪来钱,这是纳税人的钱。”我的话似乎刺激了陈,他立刻反诘:“纳税人?你纳了多少税?”狂妄的人往往是无知的,纳税人的概念怎能以纳税的多少来区别呢?隐藏在公权力后面,他们的内心其实很虚弱。
隔壁警察值班室的空调冷凝水积储在我们监室里,每天我和徐抬到厕所去倒掉,终于在 9 月 12 日晚上倒水时,我的腰部闪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没想到 13 日早上竟起不了床,稍稍一动便痛得直冒冷汗。徐见状通知了隔壁的值班警察,没有结果,我只能俯着身子,两手扶着膝盖,挪步上厕所。徐托别人为我换了一副床棚,因为原来那副已经软绵绵地凹陷下去,绝对有害我的脊柱腰椎。
9 月 15 日,办案的政保警察来了。一个年轻警察(蒋晓敏)说:“今天我们带你去看病。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吧。”接着就上来背起我的上半身艰难地向外挪动,因为我当时体重达 180 斤,真是难为他了。我的腰疼得锥心,下了楼衣服都湿透了。他们把我塞进车,汽车向一个方向开了一程,那个年轻警察又对我说:“我们先去办点事,很快的,然后再去医院好不?”我说:“好吧。”
(2007 年,这个叫蒋晓敏的人还记得我的重量,但是他当时为何要一骗再骗,可见此人心术不正。他由于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被他的主子升为处长了,以后只要唆使手下就行了。)
于是汽车立即调头向西北方向开去。沉默一会后,坐在前排一个戴墨镜的对我说:“你害了你的子女,你看方 XX 比你聪明,他退出民运,他儿子就能在省检察院工作,多少好?!”我微笑了一下。一会儿,汽车到了杭州市看守所,他们将我背进一个提审室就走了,又是陈伟星来接收。看到我被人背进来的样子,陈揶揄说:“你那副样子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被人打的。”接着陈拿出一张逮捕证让我签字,上面的日期是 9 月 13 日,一算时间,正是我腰痛的那天,难道这是一种灾难感应吗?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灾难,对我来说,求仁得仁,得其所哉。我犹如收到了一份民运资格认证书,怀着喜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几位没有看到我苍白的脸、哆嗦的手、喘喘其栗,应该有些失望吧。
(四)杭州看守所
1、“狱”字写法
做了一份笔录后,陈就叫看守所里的劳动犯(被判刑一年以下的短期犯人)将我背到监室去。送我来的汽车已经开走,车上的物品也不知去向,所谓的“看病”也成了画饼。阴暗潮湿的五区三室里被关押的人都在制作一串串的圣诞节彩灯,运往纽约普鲁克林的集装箱等着装货(监室外走廊上的纸板包装箱印着纽约普鲁克林的英语字样),为赶工期,每天的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背我进监室后,那人便走了。笼板上堆满电线和塑料灯珠,每个人面前都叠得高高的,连踩脚之处也没有。笼头说,你就躺在那地上吧。虽然是水泥地,但是擦得很干净,躺了一会,笼头又叫人拿几块纸板垫在我的身下。
笼头许华,美髯长须,因为每次提审都保持沉默,有关方面得不到口供,已经在这里关了二年多。平时他言语不多,倒是他身边的一个“破脚骨”活跃得很,以至于我一度分不清谁是笼头。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许很有幽默感,记得有一天,一个瘦老头警察来查卫生,站在走廊的铁栏杆外,向我们监室里问:“卫生有没有搞过?”大家屏气息声,无人回答。那人又更大声地重新问了一遍。我心想这样不回答问话是不礼貌的,就答:“已经搞过了。”没想到那人一听我的回话竟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一阵悻悻然走了。他走后,许笼头问我:“看你戴着眼镜,好象是有文化的样子,我问你,监狱的狱字怎么写?”我就告诉他怎么个写法。他接着说:“狱字这边一个反犬,不是人,那边一个犬,是狗,中间一个言字是讲话,畜生和狗怎么对话?他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就你懂?!”我不禁莞尔。
五区一室和二室是死囚牢,二室有一个死囚手脚被牢牢地铐在一块木板上,常常在不经意间大声叫骂。检察院来提审,就由他们监房的人抬到对面放风的地方,我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一天,隔壁放风时,二室的笼头站在我们三室的门前与许华聊天,说起他们进来后打过交道的各色死刑犯。我凑上去讲,我感觉那个死囚脑子似乎有点不正常,那笼头不屑地朝我瞟一眼,怪我多事。没多久,那死囚搬走了,因为确实有精神病。事后我想,那笼头每天和那死囚相处,应该看得出那人有病,但是,在笼子里关久了,人变得冷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生死。

2、“上上课!”
某天晚上,看守所一个姓任的副所长值班。他醉醺醺地来到栏杆前,对我进行“教育”:“你为啥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是老子,你是儿子,儿子反对老子就要拷。你看共产党又给我们加工资了,我们人民拥护它。”我说:“我也是人民,我反对它做得不对的地方是为了它更好,我难道不是人民吗?”他说:“你不是人民。”我说:“人民的概念不能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多少年来“人民”这个词被你们僭用了,失去了它的本意。”他勃然大怒,说:“老子要拷你一顿。”停了一停他又说:“老子现在不来拷你,等你走的时候,离开看守所,我来门口拷你。”然后他点着我周围的人说:“你们明朝给他上上课!”,然后就走了。
许笼头对我说:“他要我们给你上上课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拷你一顿。我们做啥要拷你呢。”他完全不像要动手的样子,而且他的话也断绝了其他噬血者的机会。旁边有个别想练练拳脚解闷的人也只能作罢了。有了解任某的人说,该人本是滨江公安分局局长,曾是专业拳击运动员,因酒后打伤在押嫌犯,造成严重后果,才降级来这里的。如果不是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今天就惨了。隔壁监室的楼华强后来与我同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谈起当时的事,他说,他们那天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姓任的家伙喝醉酒会乱来的。
任某的号召在若干天后还是产生了恶果。有一个姓李的萧山私盐贩子该人将数吨工业盐——亚硝酸钠假冒食盐销售(亚硝酸钠主要用于建筑施工、染料制造和作防锈剂。当人体内摄入 0.3—0.5 克亚硝酸钠可引起急性中毒,3 克即可致人于死地。人体一旦中毒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发生昏迷、甚至呼吸循环衰竭而危及生命,国家严禁用工业盐制作食品)。但是,该李却通过关系重罪轻判,只象征性的判了一年刑。每次被看守叫出去,他回来时总能摸出几包香烟来。
该李在许笼头调走后被看守指定当这个监室的笼头,没几天就将我打得像一只“熊猫”,那已经是 12 月 14 日,省高级法院 12 月 10 日驳回裁定后的事了。
看守——一个患口吃的警察陈一刚来调查原因,姓李的说他打我是因为我“说反动话,说共产党要垮台。”这个陈一刚结结巴巴地说:“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转身走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我 2007 年被蒋晓敏构陷再次入狱,在浙江省第二监狱遇到许华。许华说,陈一刚原本已经准备受提拔做看守所副所长了,但是,他被一名经济犯收买,为其通风报信,而后东窗事发,坏了官运、降了级。其实,早在陈一刚包庇姓李笼头时,他的贪贿就已经显露端倪了。
3、人心诡谲
看守所的生活比以前关押的地方好多了,每个月能去放风场放一次风,在石墙圈内沐浴着瑟瑟秋阳。当年草草铺就的地面已经严重风化,植物根系的力量使地面拱起开裂。残缺的墓石和水泥块的宽宽缝隙里,堆积起杜仲枯焦的落叶。我想起我度过的青年时代,就在这一道桃源岭的那边——我曾在杭州植物园工作、生活过十八年。我曾多少回放弃美丽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图书馆埋头书海;多少回在山风的呼啸中我彻夜难眠,想着中国人多少年都没有人的尊严,想着中共建政后带来的空前灾难,想着明天的出路。就在岭那边的雷殿山顶,一九七八——七九年积雪和寒风相伴的小屋里,我抄写出一篇又一篇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大字报,发出郁积已久的人的呼声。而今天,“问人生到此凄凉否?”“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易朽的是我们的肉体,不朽的是人类的进步事业,投身民运是我生命的升华。要想收获,必先播种。我深信以暴力、恐惧、欺骗维持的“稳定”不会是真正的稳定,“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阴暗、潮湿的监牢内,弥漫着一片阴郁的氛围,甚至空气也显得诡谲。人一旦降格为“犯”,更何况身陷险境,一种极端的求生本能,使人平时掩盖在那里的人性的负面情感浮现了出来。
互相猜忌,处心积虑要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优越,吹牛扯谎,就像走夜路吹口哨壮胆。欺压别人以补偿自己被强权损害的自尊心,打击别人以求得心理的平衡。
每次来了新人,他们就要来个下马威,制造种种恶作剧摧毁他人残剩的一点尊严,我知道这些人的卑劣做派就是警察暴力的衍生品,越起劲、越热衷的往往是那些被警察侮辱和损害最严重的人。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法:“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强者受辱拔刀向更强者。”阿 Q 被赵四太爷打了以后,就到小尼姑那里出气。稍没廉耻心的人便吮痔舐痈,胁肩谄笑。格言说:“谁进到了狼群里,就要学狼叫,否则就会被狼吃掉。”也许,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那么一种被动人格,倘若如此,当局就达到了“改造”的目的。我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待续)
【朱虞夫专辑】系列文章链接
2025 年 2 月 7 日上传
